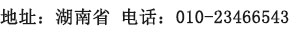对于我来讲,也许大学生活是从大二开始的。具体讲是从年暑期后的新学期。
北大之“各派”
当时的北大八十年代校园里分的是这么几派:
托派:说北大八十年代有“托派”是一件很吓人的事儿,其实那帮哥儿们姐儿们压根儿和托洛斯基一点儿不沾边,也不是北京满马路的“托儿”,虽然社会上开始流行“下海”“倒爷”,但八十年代校园里的经商气氛尚未象以后日子里那么浓厚。托派是执着准备考TOFEL的一群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走到一起来:在毕业前或后出国。出国后如何,又不尽相同。书包里装着咣啷响的饭盒,在去食堂路上念念有词,除了吃睡,其余时间都在图书馆和电教室,或用书包在这两个去处占座,这样的一准儿是托派。有诗为证:“唧唧复唧唧,有人读外语。口中ABC,听着单放机”。
鸳鸯蝴蝶派:和上海三十年代张恨水为代表的一派有渊源,都是坠入爱河。虽然此派真正厮守到毕业后的比率惊人地低,但那时实在无聊,又都有需要,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
舞派:每周末舞会,学三为胜地。慢二、慢三、快四,间以一段儿提神儿的摇滚之类。是嗅蜜的好地方。学三和大讲堂成直角曲尺型,中间栽着稀疏的柿子树,树前常停有高级进口轿车——都是来学三嗅蜜的校外款爷的坐骑。徐三儿曾见过那时珍稀如大熊猫的白色加长林肯,回宿舍后和我们赞叹不已,说不知哪个蜜傍如此大款,为北大增光。当然也有望着学三车林恨恨不已大叹世风日下的,多是老教授。(注:鸳鸯蝴蝶派和舞派时有交叉)
麻派:麻派就是打麻将的一伙。多年以后,我去成都,满大街都是坐在竹椅上打麻将的,全是一身精瘦排骨的男人,面有菜色,一群群的。看那阵势,不由想起北大麻派。下面是北大麻派的故事。
麻派
三十二楼四零八,我一生也不会忘记的地方。“黄昏的树影再远,也离不开树根”。(此处引用神书《精神的魅力》)
我们宿舍的哥儿几个,除了白天必不可少的上课和吃饭外,就是躺在床上睡觉。不舍昼夜,昏天黑地。我以后再也没睡过那么多觉了。晚上十一点全楼熄灯,四楼楼道里煞是热闹:几个块儿大的家伙把哑铃和拉力器纷纷亮出,示威似的开练,我就奇怪,越是结实的哥儿们越爱显示其上身肌肉。
水房里冲凉的,伴着一声惨叫,把整盆的凉水劈头盖脸浇下,然后某水房歌手开始每晚照例的演唱。据确切消息:全楼音响效果最好的地方就是水房。
再晚一点儿,又有人扛着脑袋在走廊里游走无定,时而引颈狼嚎。
白天,没课,无处去。全体躺在床上听歌,当时流行苏芮、齐秦、王杰,再后来是罗大佑、李宗盛、崔健和黄舒骏。大学里可能听了我一生的盒带,每每在各种歌声里进入迷离。于畅的一个国关的同学周日来,一览此情此景说:“你们丫北大也太颓废了……”
话说那年夏秋交错之际,周老大闲极无聊之中一时兴起,用貌似挺贵重的草绿色毯子包着副麻将推门闪了进来,这应该是北大麻派一支重要力量的历史时刻。三十二楼四零八的第一次麻将比赛也于次日早饭前结束——那天是周六,不熄灯,周老大轻轻地挥挥手,把麻将和毯子留下了,却带走一大片云彩——许多零钱和菜票,从此以后,三十二楼四零八就成了一间著名的"麻屋",那毯子也就成了专业“麻毯”。毯子以后还换过几次,也都还凑合,但总不像周老大的麻毯那样有一种仙气。
周老大来自安徽安庆,安庆还算有点小名气,除全国著名的黄梅戏之乡外,历史上好象太平天国时也发生过重要战役。他常夸自己酷好乒乓球,是高中时学校冠军,大家混熟了以后,不知怎的得个外号叫“安冠”,意为安庆市兵乓球冠军,外人一听都大惊,真是人不可貌相,你怎么能发现自己身边瘦骨嶙峋的这位麻手居然是安庆乒乓球冠军呢?也愈发觉得北大真是卧虎藏龙,但是麻坛周边少乒乓球好手,没法和“安冠”较量一下。
北大是这样的,一般不服就要约着拼一下,我大一和恩富拼围棋,一上来居然死了六十多子。我高中时因景仰中日围棋对抗赛中抗日英雄聂旋风,很是酷爱一阵子围棋,一直照着每期《新体育》上的棋谱打谱学习,自以为入门了。哪知,唉……从那以后,我再也不下围棋了——没法和那帮人练。
一次挑灯夜战,周老大手气极佳,一高兴自嘲道:“我是安徽省安庆市枞阳县某某中学高一三班小组乒乓球比赛冠军,简称安冠。”他自己说,刚进校时想进校队,结果让当年校队女队员暴催(北京方言,念四声“cei”)两局,每局仅拿十分左右。但不管怎样,安冠因麻瘾大、名字顺口,倒在麻坛小有点了名气,其经典形象是:“腰里别副牌,见谁跟谁来。”某麻派名人曾说:“安冠,我第一次听说你,把我吓一跳,以为你擅长开暗杠,所以叫暗杠冠军呢!”人就这样,喜欢什么联想什么,麻派像东北胡子似的有自己的黑话,比如,五饼叫“四菜一汤”,七饼叫“歪把子机枪”,两万叫“肖兵”,三条叫“裤衩”等等,都是典型的象形文字。
三十二楼四零八
介绍一下三十二楼四零八吧。
四零八老大徐三儿,长春人。高中同学都叫他三儿,我们觉得这名字明显有东北人的匪气,决定叫他徐三儿,这样听上去善良得多。徐三儿开始觉得别扭,后来就习惯了。他和他媳妇儿热衷于打二人扑克,长期坚持,乐此不疲。要回忆大学时代,徐三儿两口子盘腿对坐在上铺打扑克的情形应该是印象深刻的一幕吧。放单儿时,他就靠在床上戴耳机听英文歌曲。徐氏高论之一:听英文歌曲是练习听力的最好方法。后来一直听VOA,不但听力练出来了,口语也成了地道的美音,感叹有人花一百块买双阿迪,说难以想象,“不过,”过一会儿又道:“穿上确实有型。”吃海鲜过敏,喝啤酒也过敏,大家就坚持不懈地锻炼他喝,过敏症好了,酒量居然甚豪。能背诵多阕宋词,与何晖、恩富车轮战,结论是术业有专攻,各有千秋。
老二于畅,北京人。系出名门——北京四中。于畅著名的典故是某夜睡梦中唱歌:“我独自在风雨中……”,挑灯夜读武侠的张伟听了个一清二楚。苦心人天不负,终于有所建树,第一届北大校园歌手大赛,于畅以《恋曲》名列第八,徐三儿吉他伴奏。
张老三,张伟,安徽六安人。第一次知道六安瓜片是名茶,泡开在饭碗里(大家普遍没有茶杯),舒展的密密层层,当年谁会品茶呢?品不出佳味,我们称之为树叶茶。
四零八靠门的下铺从入校后一直空了很久,以为要五个人过这四年,张老三姗姗地来了,他哥送来的。虽然都戴眼镜,哥俩却不太像。哥是北大生物系研究生,比张伟矮,典型南方人。我老说张伟南人北相,主要还是在性格上。张伟欣然曰:“南人北相主大富大贵!”
张伟在家住院来着,十二指肠溃疡,很稀奇的病。后来在校不规律地生活,却一直没有犯病。可是放假回家老是复发,“我毕业分配看来只能要求留京,没办法,回家水土不服。”他出故事最多。恩富武侠租书铺子开业后,大家狂读金庸、古龙。“古代!”这必是读到酣处有所感而发:“古代多好!人都住在山上。”继续读,一会儿,恍然大悟般:“我说怎么这么黑呀,嗷,原来没开灯。”满室哗然。和大家一样爱好啤酒,当时量浅,第一瓶尽,脸红。第二瓶始,手握啤酒瓶左右晃,时不时的在桌上重重一墩:“啊——颓……”拉长尾音,余味无穷。其实我有时挺火的。”醉态可掬。几乎所有朋友都爱和张伟喝酒。
老四小陆,上海人。喜欢在铺上戴着耳机,开最大音量狂听粤语歌,然后香甜入梦。上铺的徐三儿时时捶床大吼:“小陆!把你架子鼓声音关小点儿。”不知道多年以后小陆的听力有没有受影响。
老五老刘,山东青岛人。其实是全班年龄最小的三人之一,不知为何被尊称老刘。倔强,时不时地狂怒一下,又被爱称为“老驴”了。这厮也无甚长处,倒是熟读金庸古龙,但经过四零八室的普及武侠知识运动,大家水平都差不多了。爱淘旧书,从海淀、王府井至琉璃厂。何晖同有此癖好,每见好书奔走相告,欣然携手同往。尤喜涉猎历代笔记小说。某日与何晖人购一册《四十三侠客传》归,何晖随手检一页诵读,才数句,“这是昆仑奴一则”老刘说。“大侠!”何晖大惊,翻身下床,拱手连连:“佩服,佩服。”老刘即是在下。
来自武汉的何晖原本是四零八的老六,甚是了的。出身武汉经济学世家,专业藏书大概和教授们一样,他读专业书是拿一支彩笔在书上一路划下去,划完也读完了,和一目十行也差不多吧。大卫李嘉图、芝加哥学派弗里德曼、哈耶克侃得我们是一楞楞的,后来改和老师们侃,结果,上微观和宏观经济学时,经常老师讲上半场,何晖讲下半场。都奇怪他为何不直接报考北大硕士。全班称他为何大侠。
大侠在张伟上铺。“你们快打麻将吧,听着麻将声我看书踏实,真的。”又是奇人怪论。我想他是锻炼自己在嘈杂环境中的定力,毛主席年轻时也这样。何大侠定力不如毛主席多矣。他终究还是搬到对门儿四零七了。不知道这算不算劣币驱逐良币。“何大侠是我们四零八的骄傲,永远是。”都这样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何晖注定是要来重振经院乃至中国经济学界的。
何大侠把四零七的恩富换过来。所以恩富是老六,也是老七。
陈恩富,浙江台州人氏。不知哪堂课上,老师点名叫他陈思富,思富就是想富,大家也叫他陈想富。浙江自古多才子,恩富更是兴趣广泛,文武双全,开始就神出鬼没,独行侠样,其实是在后湖僻静去处练武。班里第一次聚会,八仙过海,恩富打趟地躺拳,身手矫健,他那时比后来瘦五十多斤,最后鲤鱼打挺没起来,四面抱拳说:“兄弟今日失手,见笑。”俨然街头艺人。
牌气最好的也就是他,老被张伟调戏。
最厉害的是他的三个大爷,赫赫有名:吴清源第一,是喜爱围棋的缘故,收有吴氏全套棋谱。当然,吴清源老先生的棋品人品没的说,高山仰止。金庸第二,四零八武侠运动的结果,是大家对金庸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罗大佑第三,一代人听着罗大佑的歌走过大学时光。恩富最大的贡献是大二时搜罗了数量可观的武侠书,就在四零七开租书铺,我们都去看书,当然只限于看金庸,后来加入古龙。恩富搬入四零八,也可能是因为这里全部是武侠迷,大家可以没日没夜地大侃武侠。
武侠世界
上句“飞雪连天射白鹿”,下句“笑书神侠倚碧鸳”,四零八人对接头暗号样一唱一和。
大家以前多少都读了金庸,起码是几个长篇。现在有机会全部系统重读一遍。谁要问哪本书怎么样,“真羡慕你,金庸这么好的书都没看过。”徐三儿老是来这么一句。“可以从头慢慢欣赏。”徐氏高论之二。
一般是从晚上八、九点开始。人齐,开始讨论。大家全攻的一本书《笑傲江湖》,第一章灭门,每人细读一遍,抛开书,出题互考:福威镖局门前匾额有几字?如不细看当然是“福威镖局”四字,答案却是六字:福威镖局,旁边俩个小字“总号”。
我现在仍能背出独孤九剑总决:甲转丙,丙转庚,庚转癸,乾坤相激,震兑相击,离巽相击……
青山磊落险峰行,玉壁月华明,马急香幽,崖高人远,微步觳纹生……千里茫茫若梦,双眸灿灿如星……真是纸醉金迷。不好好上课学习,原来这帮家伙都把精力用到这上面去了。
往事如烟
写点东西,或者进行麻将业务时,安冠一直抽七毛八一包的不带把春城,也是正经云烟呢。
本地烟,金健、长乐风行一时,红白相间烟盒的长乐据说专杀精子,号称避孕烟,被无情抛弃了。年,应运而生的亚运烟。各种平和的云烟,价高难得。状如土炮的便宜雪茄,烟嘴发甜,抽一口,“嘣!”像挨一拳,偶一为之。
烟摊儿上,走私烟上品自然是长希短万——长嘴儿希儿顿,短嘴儿万宝路,不知何故,都认这口儿。还有纯白大剑——KENT,现在已罕见了,那时可是身份象征。
恩富、小陆回家总能带回几包好烟回来,大家过年。恩富把最后两包短万藏在褥子底下,没人时偷着过瘾,被心细的张伟偷个正着,大家均了贫富。晚上恩富一边看书,一边把手伸到褥子底下摸烟,一看,还剩一根儿,大叫:“早晨还是满满的一包呀……张伟!”大家偷着直乐。
于畅最早告别糙烟的,只抽外烟。夜深人不寐,烟瘾大发作,挨到恩富床根儿:
“恩比诺,来根烟的。”
“只有亚运90。”
“真的?”
“真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恩富笑眯眯的,眼睛都笑没了。
“你什么时候不骗我?”
于畅捏着90,像捏着苦药,皱眉:“太糙了,都没法抽。”回头扔还恩富。只得到外面去找,挨着宿舍找可能趁好烟的主儿。半小时后,叼着根万宝路洋洋而归,躺下,在枕边蜡烛上点着烟,深吸一口,慢慢喷出,屋里就有了一股万宝路的糊味了,一边舒服地长叹一声。哥儿几个那是什么鼻子啊,都闻烟味赛闻饭香的主儿,纷纷嚷:“于畅!有短万别自己咪了,来一根儿啊。”于畅早已坦然睡去,枕边白蜡在风中摇曳。他把蜡烛点在硕大的录音机上,每在烛光中入睡,不是什么好习惯。终于一次,蜡烛燃尽,把录音机烧掉大块,差点火烧连营,不过录音机居然还响。
生命之源
“啤酒是我生命的源泉。”安冠像先知布道样总结道。
我们坐在三十二楼后石凳上,条石上摆着四瓶冰镇红贴五星,一人一包水煮花生米,可消漫漫长夜了。虽然都晚上十点多了,因为是周末,周围楼里依然人声鼎沸,灯火通明。有过大学生活的人也许都一样,周末一定熬夜,早睡觉好象觉得吃亏,不知为何。我现在仍有这习惯,周未总得干点什么,要不就呆着也行。
喝酒的去处是我和安冠常去的三十二楼二十八楼间的空地,周围一圈高大的核桃树,秋天枝头会垂下累累的青皮核桃。边喝边聊,看匆匆行人,听自行车铃响个不停,
“你说都忙什么呢?他们。”
“这里是小桃花源呢!”俨然两个避秦的世外高人,自得其乐。
啤酒喝的常是白贴北京,红贴五星。燕京那时卖的差远了。啤酒这东西真是,后来燕京一不小心居然火了,大街小巷,全喝燕京,莫名其妙。开始喝楼下小卖部老陈的啤酒,后来发现老丫的居然把过期的啤酒卖给我们,都酸了,问他,哼哈地假装糊涂。恨得我们牙疼。夏天就偷他店里的西瓜,边吃边说:“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后来老陈新买的自行车丢了。这可不是我们干的,不知是哪路被惹恼的人马下的手。老陈的小卖部不大,柜台外几张桌椅,可供小酌。在这里能见到各路人马。学四的两个大师傅每天晚上来喝,混熟了,一块儿撮麻,后来打饭倒省不少花费。
人多时,取了吉他,抬一箱啤洒到更好的去处喝。夜色下的图书馆草坪,点缀着几株落叶松,饱含沁鼻青草味的空气更觉清新。席地而坐,喝酒、吹牛、弹琴、唱歌,神仙生活。
徐三儿弹崔健,大家乱哄哄唱《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一块红布》、《花房姑娘》,一曲终了,都不吱声,似要细细品味这夜色星光,美酒草香,永留这份心情。
酒酣,换了安冠,弹起简单的和弦,大粗嗓子怒吼:
“今天又是星期天,星期天,
冷冷清清是校园是校园,
北京同学都回家去团圆啊,
留下俺这外地人受孤单。
不想看书也不想做实验,
不见老师也不见辅导员,
泡上一袋方便面越吃越饿,
点上一支大重九越抽越烦。”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以下琴声突变:
“今天又是星期天,星期天,
热热闹闹是校园是校园,
校长书记来宿舍问寒问暖,
教俺无产阶级人生观。
俺爹俺妈在家里盼望俺,
俺弟俺妹在家里羡慕俺,
大道理和小算盘俺岂不知,
俺只怕过这星期天啊星期天。”
安冠说这是传自八七级的北大校歌,但是我们怎么听都象一首山东民歌,实际上,这首歌只听他一人唱过,我怀疑是他所独创。勺园的几个日本留学生在草坪不远处大唱古怪的日本歌,素怀抗日大志的我等甚觉刺耳,加大嗓门,又来一曲《从头再来》,最后干脆《国歌》,直到把小鬼子们哄走了事。
偶尔,一人凑十块钱,可以到校外的小酒馆撮一顿。小南门儿不远处的朝鲜冷面,马加力的熘肝尖,最常去的是“毛毛”。
看书到深夜,谁问一句:“恩富,饿不饿?”
“饿,怎么着?”
“毛毛?”
“毛毛就毛毛。”一时响者云集。
楼门已关,一楼厕所天窗成为昼伏夜出者的门户。一个个爬窗出去,兵发毛毛去者。为了省钱喝酒,菜尽量点便宜经吃的,比如要三盘麻婆豆腐之类。
也有次噩梦,是罗比拿了第二届北大十佳歌星第十,众星捧月簇拥着新诞生的歌星到“毛毛”庆祝。吃涮羊肉,喝了啤酒不计其数。撤退时,为一点儿屁事儿动起手来。不堪回首啊!“毛毛”再也没有去。
那年世界杯
“那年世界杯,我们还看着电视,为了足球明星共同欢呼……”
巫启贤的这首歌现在听不到了。年我第一次看世界杯,竟然成为有些忧伤的回忆。大学永远和足球结缘。有电视的宿舍很少,新生到研究生楼蹭球看。我看年足总杯决赛是和二十多人挤在一起看十二寸黑白,末日王朝对英甲桑德兰。年轻的盘球王子麦克马纳曼、巴恩斯、拉什……
年世界杯,电教已经开放。徐三儿看好巴西,恩富是坚定的德国派,老叨比克林斯曼什么的,张伟好象也是巴西荷兰的。也许因为马拉多纳,我看好那时不在状态的阿根廷,独树一帜。
看球,也是打赌。
最精彩的那夜记忆犹新,巴西--阿根廷;德国--荷兰,1/4决赛。
在“毛毛”,巴西全场优势,但卡雷卡、贝贝托得势不得分,马拉多纳星光闪烁主宰世界,一记天才妙传,仿佛印第安人的“风之子”卡尼吉亚一剑封喉,将永远是夺冠热门的巴西扼杀。球入网后,一名巴西黄衫美少女黯然垂泪的镜头成为今后多年的经典。而在“毛毛”观战的诸位,除了我,都目瞪口呆。接着德国三架马车马特乌斯、克林斯曼、布雷默撞翻荷兰三剑客古力特、巴斯滕、里杰卡尔德,又生擒夙敌无冕之王。沃勒尔和里杰口水大战,双领红牌,桔色大军拥趸气得直嚷:“沃勒尔真是狗屎,沃屎,你丫敢碰我们里杰!”这沃屎和里杰现在已经分别执掌两国国家队帅印。
阿根廷凭着好运,戈耶切亚神奇地连扑点球,闯进决赛,又终于倒在布雷默的点球下。那一届的阿根廷人员不整,踢法粗野,比现在叱咤风云的阿根廷差得远。
年世界杯真是明星云集:利特巴尔斯基、哈吉、勒克图什、斯托依科维奇、布罗林、进球翻跟头的斯库赫拉维、莱因克尔、加斯科因、米拉大叔和伊基塔……
四年北大生活短暂也漫长,平凡的我们在那个不平凡的年代任性地挥霍青春。虽然有过很多遗憾,也还是有闪亮的点点滴滴,值得每一个人午夜梦回。
一稿于九十年代
二稿年5月11日
挈妇将雏鬓有丝于青岛
年毕业前夕一塔湖图
左起:刘志辉、张伟、王春林、徐三鹰、陆志军、于畅、陈恩富
刘志辉88国经平凡在不平凡年代任性地挥霍青春
赞赏
人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