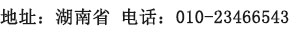鍖椾含鍝姝h鍖婚櫌娌荤枟鐧界櫆椋? http://wapyyk.39.net/bj/zonghe/89ac7.html我妈跟我说,小区二期的烂尾楼有人接手了。可是第一天施工,就在场湾那一片荒地里挖出来一具尸体。尸体完好而安静地仰面朝天躺着,周边全是方便面袋子和火腿肠塑料皮,吓得建筑工人鬼哭狼嚎,非要找包工头加工钱才肯继续干。小区里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死的是谁,可是大家都绝口不提。我九岁以前,只有两个爱好:下象棋、打牌。六岁起,我就因为这两个爱好红透了整个村子。我们全村老头儿都致力于轮流拿着马扎跑到我家的凉棚底下向我挑战,可是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被我杀得茶饭不思,几乎要失去了生活的勇气,还有的索性趁机说自己急火攻心,气得好几天都不能下地干活儿。六顺比我大十六岁,是我们村里最帅的无为青年,肤色挺白,少言寡语。他也只有两个爱好:老老实实观察我跟各种各样的老头儿在象棋桌上厮杀,积极替补打牌桌上被老婆突然叫回家刮土豆的包。尽管我们俩的爱好恰好在同一领域,但是因为我六岁,理所当然地被传成了的一代神童;而他二十二岁,只能被唾骂成了一个不学无术、游手好闲的懒汉。尽管如此,六顺对此毫不在意,因为他懒得张嘴,所以我也无法听到他对此事的任何辩解。如果实在是被我问急眼了,他也有对付我的方式,就是微笑——持续缓慢的微笑,牙齿绝对不会露出来,嘴唇上的八字胡会顺着一个表达微笑的弧度微微翘起来。后来看到《疯狂动物城》里的闪电时我伤感地想起他。我对此也毫不在意,而且我十分讨厌街上的老妈子因此对六顺评头论足。我还偷偷向我妈表达了我的观点:长得好看的人,自然有与众不同的活法,他们就应该忙于把自己输送到各个热闹的角落去展览,去供养并陶冶众生的审美,犯不着跟其他人一样非得靠劳动致富。我妈听完毫不客气地踹了我两大脚,还说让我以后离六顺远点儿,懒是病,能传染。六顺每天早上七点钟会穿上一件白衬衫,袖子上的扣子要扣到手腕,然后跟上班一样,背着手带着马扎来到我家的凉棚下,直挺挺地坐好,迎接这一天的美好。为了不招致我妈的反感,他会主动掏出钱来我家小卖店买一包青州烟,等七点半能凑齐一桌后,他就挨个儿给大家分烟,所以打牌的那帮人,挺喜欢他在旁边待着的。六顺像个聋哑服务生,光干活儿,净微笑,不说话。我放学后,会主动跟六顺打招呼。他就像一个对我倾注满满希望的老爷爷一样,朝着我一边点头一边“啊”一声,然后两眼放光地看我把书包一扔,一屁股坐下来,把这帮老弱病残们杀个片甲不留。等人群将要四散而去的时候,大家都会以输惨了为名,极不耐烦地把牌和棋子儿使劲往中间一堆,甩手走人,分分钟作鸟兽散。只有六顺,他会耐着性子帮我收拾残局,并把所有的马扎归拢到卖店旁边的小仓库里去,然后连个再见都不说,帅而优雅地绕过一根电线杆,迈着一个成功小白领式的悠闲步伐,亦步亦趋地消失在路的尽头。劳动人民最看不惯大闲人,但是人家六顺跟着他妈妈和哥哥有吃有喝,也不向任何人伸手要钱,所以他们再怎么看不惯,也无法拦着他安逸地长大。一个黄昏,我放学后,三下五除二,在十分钟内干掉了赵大爷从邻村请来的无敌棋王九哥。九哥之所以是九哥,是因为年轻时他在赌局上输掉了一根小指。六顺看到我势不可当地将战火燃烧到了邻村,在旁边高兴得像一只兴奋的大猩猩一样前仰后合地拍着桌子,冲着我猛竖大拇哥。这时候村子里突然跑出来一个人,站在村口的磨坊前,冲着六顺大声喊:“六顺,六顺,你家出事儿了,你快回去看看吧!”六顺“腾”地一下站了起来,喃喃地说了一句:“谁死了?”牌桌上的人面面相觑,都说,傻小子怎么这样啊,要么不说话,要么乌鸦嘴。六顺拽了拽白衬衫,双手抱拳,向我们一一辞行,然后运了一口气,蹲在地上,以百米赛跑的姿态,将自己迅猛发射了出去。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从不缺席的六顺都没有出现过。九哥骑着拉水的三轮车路过我家的时候,一下拉了手刹。在三轮车上东张西望了半天,确定他老婆不在附近后,便从三轮车上跳下来,坐在门外的破沙发上抽烟。他说他最近活够了,他本来以为自己到死都天下无敌了,临了还让一个黄毛丫头给灭威望了,连村西头的赵寡妇看见他的时候也不主动娇滴滴地喊他一声九哥了,昨天回家邻居家的鸡都飞奔过来要啄他,这一桩桩一件件,他一想起来就根本咽不下去饭,这几天他老婆还天天撵着他去地里干活儿,但是他一面朝黄土就更觉得自己实在是窝囊。“那九哥你想干吗?”我转身从屋里拿出来一袋方便面,边啃边忍不住问了九哥一嘴。“咱俩再下一局。”九哥吐了个烟圈,气定神闲地注视着远方。“再下你也是个输。”我头也没抬地把话头接过来,用牙齿把方便面调料包咬开一个口,左手碾碎方便面,右手倾洒调料。“小丫头,这么小不宜锋芒太盛,给你讲九哥这指头是咋没的。”说着,九哥就把少了小指的右手伸到我眼前晃。“九哥,你快别拿你少根指头这事儿忽悠人了,这是你的耻辱,又不是你的骄傲。你就说,你到底想干啥吧。”九哥一听,一下憋红了脸,往四周偷偷瞟了一眼,压低了嗓门儿小声说:“咱再多叫点儿人来,当着大家的面儿,你放放水,输我一局。九哥这辈子就活这一张颜面,你小丫头输给了谁也不觉得是个事儿。这事儿办成了,以后有需要九哥的地方,尽管开口,九哥保管给你办了。”“那行,我有个条件。”“啥条件,尽管说,只要别跟九哥要钱花,九哥的钱全让你九嫂攥着呢。”“我不要钱。你叫人的时候,也把六顺叫来,他在,我就输给你。”“六顺……他估计来不了。”“六顺到底咋的了?”“他妈死了。”“他妈死了?他妈死了,他为啥连门都不出了?”“你还小,说了你也不能明白,跟你说多了,你妈还得找我算账。”“九哥,九叔,九大爷,你快说,别看我小,就没有我不懂的事儿。”“六顺有恋母情结。”“啥?那是个啥?喜欢妈妈?”“对!但不是那种单纯的喜欢。”“喜欢妈妈就是恋母情结?”“跟你解释不清楚,就是因为太喜欢妈妈了,而产生一种特别的情愫。”九哥是邻村少有的江湖人,会整的文化词格外丰富。“你要说不明白,咱这事儿就免谈。”“差不多就是把妈妈当媳妇了。”我一听,吓得差点儿让方便面渣渣呛死,瞪大了眼睛看着九哥:“九哥,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反正你们村的人都这么说。你赢了我那天,六顺妈妈突然脑子出血,本来就高血压,脑壳里的血出不来,压迫脑组织,就死了。从发病到死才一个小时,六顺回去的时候,人都凉透气了。”“那怎么没听见村子里有人出殡啥的?”“六顺不让,还因为这个跟他哥哥分了家。”“为啥,不下葬不就臭了吗?”“谁说不是。他不让,村里的白事儿长老谭老爷子找他去商量白事儿,被他一把推了出来。”“哎,毕竟是亲妈死了,可以理解。只是屋里放个死尸同吃同睡的,即便是自己亲妈,也是怪可怕的。”“一开始村里人都带着白事儿份子钱去他家,一进门就看见六顺躺在他妈妈旁边,绷直着身子,乍一眼看上去,像两具尸体似的,吓得送钱的人,放下钱就跑。关键是大夏天的,都嗡嗡招苍蝇了……”没听九哥说完,我就朝着下水沟快速地跑过去,蹲下来不遗余力地把一肚子方便面全吐了出来。九哥在身后惊了一下,过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可惜,可惜了啊。”也不知道是在可惜六顺的大好青春,还是在可惜我刚才吃下去的那袋方便面。十天之后,六顺突然出现在凉棚下,这次他没有穿白衬衫,连鞋也没穿,光着膀子赤脚走在柏油路上,烫得他走两步跳两步,内裤松紧带扎到了腰带的上边,像一只上了油锅的鬼。这次他没有买烟,也没有随身带着马扎,头发就像刚被炸过一样,目光呆滞地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来几十块钱,递给我妈,说:“姨,买东西。”我妈一看六顺这五迷三道的样子,战战兢兢地接过钱来:“你要买啥?咋拿这么多钱?”“方便面和火腿肠。”“全买了?”“嗯,全买了。”“买一半吧,留下一半的钱,吃完再来。”“不了,就全买了。”在五毛钱一包方便面、一块钱三根火腿肠的年代里,六顺用二十多块钱买了两大袋子粮食,晃晃悠悠地回了家。路过的小孩艳羡地扭过头目送他远去,那天的野狗也欢腾着追了他三条街之远。一路上,他在阳光下闪耀着富足的光芒,却转身走进了一座茅草屋的荒凉。村里人都说,六顺要冬眠了,可是我不信,因为我还穿着短袖和裙子,这明明是夏天。六顺走后,我就去找我妈算账:“凭啥不痛痛快快卖给六顺东西,是不是瞧不起人家?”我妈毫不客气地又给了我两大脚,说:“六顺需要多出来几趟,一下子买完,吃不完坏了是一说,要是指望这些东西把自己养在家里,小伙子就废了。”我觉得我妈说得有一定道理,于是顺便提出了去看望他一下的要求。这次我妈没有再给我两大脚,只是说,过两天,她亲自带我去一趟。后来我才知道,我妈说的过两天,是在等六顺把他妈下葬。六顺的手纤长灵巧,爬起树来身手也十分敏捷,尽管他最近消瘦了不少,但是依然扛着大铁锯把村里最好的三棵楠木锯倒了。六顺叮叮当当地在家门口敲打了一个星期,把锯来的木头做成了一具熠熠生辉的棺材。他站在邻居家门口愣了会儿神,看着夕阳一针一针刺入他的毛孔,一下就冲到邻居家的院子里掐走了所有的红色花头的月季花。六顺用大红花儿铺满了整个棺材底,转身又去灶王爷的供奉台上拿下来一挂鞭炮,举着竹竿就去门口轰轰烈烈地放了。村里人听到了鞭炮声,都知道是六顺妈妈要下葬了,于是赶紧呼朋唤友地去看热闹,但是很多人看完往家走的时候,差点儿把肠子都吐了出来。六顺的妈妈因为长久没有下葬,所以身上生蛆了。六顺抱他妈妈进棺材的时候,还有活蛆爬到了六顺的胳膊上。小白蛆弯来弯去,六顺并没有将它们驱逐下来,而是拿在手心里看了半天,眼睛里流出了热乎乎的泪水。六顺把妈妈葬在了院子里的杏花树下,大坑挖了三米深。有些看热闹的人带来了铁锹,可是真正埋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上手,大家都觉得太瘆人,于是都眼巴巴看着六顺一锹土一锹土地埋,直到余晖洒进院子,六顺用脚将葬母的地方一脚一脚压实,然后“扑通”一声跪了下来,说:“你用母乳喂了我二十七个月,我就该给你守孝二十七个月,但是看着你一天天腐烂实在于心不忍,所以把你葬在杏花树下,从此儿子为母亲守三年之孝,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我当时太小,根本听不懂六顺到底说了些什么,但是又很奇怪地一字不落地记住了他那天说的话。后来我学了生物,专程跑去看那棵杏花树是否更加茂盛,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微生物能把尸体分解成植物需要的营养物质和无机盐。可是我却一直无法理解那天在杏花树下六顺对他妈妈说的那些话。后来的后来,我走在大街上,像无数平常人一样路过杏花树,没有人看得到我心中的包袱,而我却一直记得那天,有少年双膝跪地,说守孝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六顺从此真的不出门了。村干部带上从集市上买的新鲜蔬菜和活公鸡去了他家,六顺不说要,也不说不要,只是静静地躺在床上,听虫鸣鸟叫,看花荣花败,眼神木呆呆的,再也不打算去看任何人一眼,像是下定了决心要跟时间斗法一样。所以,去看过他的人,都摇摇头劝别人不要再去,说六顺被心魔控制了。一天下午,我妈赶集回来,我挑了几个熟得最好看的西红柿,在衣服上抹了两下,拉着我妈就要去看六顺,我说我觉得再不看他,他就要死了。我妈伸手从货架上拿下来两袋蛋糕和两袋点心,我赞许地对我妈点了点头,暗暗感叹这么一个平常对我抠门抠到经常因为一毛钱零花钱就要对我大打出手的妇女,关键时刻竟然十分敞亮。事实证明,我妈不但敞亮,而且也聪明。那天我们推门进去的时候,发现地上的蔬菜烂了一地,被绑着腿的活公鸡因为六顺对它的冷落早已气绝身亡。六顺的床上泛着一股子极浓的尿骚味,我捂着鼻子往前凑。“六顺哥,你倒是说句话嘛,九哥因为你,到现在还没翻身呢。”六顺直着身子,悠悠地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一眼我妈,突然就满眼泪水,身子抖了一下,想翻身背对着我们,却因为虚脱没能成功,他想努力把自己从丧母之痛中拉出来,却又不得不陷入了旧时光。我虽然不理解六顺对自己妈妈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情感,但我以前一直以为,通常情况下,男人如果失去媳妇儿,都会再换一个媳妇儿来疗伤,如果失去妈妈,也似乎没有什么大不了,因为我们叫他们一声大男人,他们就不得不收起痛苦,马不停蹄地继续上路。我妈拉了我一把,想把我拽出去,结果后退了一步,不小心踩上了一坨黏糊糊的屎。我妈叹了口气,只好低头拿起一块土坷垃把屎从鞋子上刮掉,说:“自己不想出来,谁也拉不动你。”说完就把点心和蛋糕往六顺的床头推了推,拉着我走了出去。跨过院子门口的木槛时,我踮起脚来趴在我妈耳朵边商量了件事儿,我妈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又说了句瞎折腾,后来就由着我把家里的象棋拿到了六顺家。一个人努力去适应不适感的时候,会变得出乎意料的强大,就像是你不想失去却不得不适应失去,你不想长大却不得不适应长大一样,一切都在你的抵触情绪中变得越来越自然,让你来不及察觉自己的微妙变化,它就马不停蹄地成了你人生的一部分。等我跑回六顺家的时候,发现他正躺着疯狂地吃我妈带来的蛋糕,这时我才知道,其实我妈早就知道六顺家里并不缺生活起居的用具,只是他不想烹饪,不想燃起袅袅炊烟,他不想自己独立面对生活,他只想吃信手拈来的熟食。在屋子里待了才十分钟,我已经完全闻不出屎尿味儿来。我在旁边自己跟自己下棋,他在吃着蛋糕,我们互相不说一句话,他对胜负再也提不起兴致。后来我跟自己下成了平局,于是左手握住了右手,自己跟自己讲和。六顺没有看我,帅气的八字胡已经长成了生日蛋糕上那种寿星爷爷才有的大长胡子。他眯着眼睛看了我一眼,微翕着嘴唇想要说什么,却又生生咽了下去,眼睛里一下憋出来一股眼泪,顺着眼角一直在淌。我突然看到他脚上有什么东西在爬,我凑上前去,掀开毯子一看——六顺的脚腕上竟然爬满了虫子!我被吓得边跑边哭了一路,晚上做梦哭得嗷嗷叫。我妈找神婆子给我叫了好几遍魂,逼着我吞了一大碗烟灰,但我依然是经常发烧说胡话。我每天都会问问我妈:“六顺为什么会这样了?他脚上已经全是虫子了,活人生了虫子,不就离着死不远了吗?”我妈回答不上来。但是村子里的人绝对不会放过这样一个自甘堕落到极致的人,大家都说,谁家里还没死过人,谁还没失去过亲人,他这就是懒,不愿意劳动,故意一蹶不振,总是指望着他妈妈养他,现在妈妈没了,他就只能懒死了。我真是恨透了这帮人的嘴,瞎说起来永远都不管不顾的。为了表达愤怒,我找了班上几个喜欢我的小男孩,亲了他们一人一口,又给他们一人发了一个面具,让他们潜伏在路边,在放学路上,打了那几个嘴碎妈妈的心肝宝贝。我想,她们自己家孩子蒙受委屈嗷嗷大哭的时候,她们作为妈妈是不是能了解什么叫作心痛?有人说,六顺要死了,他是真的活活懒死的。他已经整整在床上拉尿半年多了,整个屋子里都爬动着与活人为伍的虫子,大门一直是开着的,每个经过的人都会往里看上一眼,然后回家跟孩子说,你就懒吧,早晚懒得跟六顺似的,身上生蛆,活活懒死。最后一次去他家,是一天下午放学后。我随身带了一把剪刀和一把从医务室买来的消毒刀。六顺的房间里已经堆了一地吃的——生的、熟的,可是他几乎都没有动过。他瘦成了火柴杆一样,骨骼凸起。我跟六顺说,我已经看了很多解剖学和生物学的书,了解到身上的腐烂处是要切割掉的,我虽然不敢动大手术,但是愿意帮他处理一点腐肉,省得让虫子拱烂了。我看六顺没吱声,也没有阻止我的意思。他的大眼睛深陷在眼窝里,喘气的时候看上去十分痛苦。我跑到院子里调整了几次呼吸,换了几口新鲜空气后,气贯长虹地进了屋子。掀开六顺被子的时候,发现他的脚肿得像是一个足球,脚面已经看不出来了。我看着六顺的眼睛,再一次征求了他的意见,他依然不动声色,回我以静默。我只好拿起小刀来,轻轻地扎了下去,结果“哗啦”一下,六顺的脚就像是装了液体的皮囊,皮囊中的液体淌了一床。我捂着嘴巴看了一会儿,又看了一眼六顺的眼睛,他又开始流眼泪,还紧紧地闭上了眼睛。那天,我才知道,他之所以不下床,是因为早就走不了路了,他的脚踝里灌满了脓水,看似是有一双脚,实际上早就隔着一层皮,腐烂了。他放弃了行走,所以他的双脚也放弃了他。第二天,有人来我家买烟,告诉我妈,六顺今天一早死了。我哭着把昨天的事儿告诉了我妈,说六顺是让我弄破脚才死的,我妈说,别傻了,六顺早就死了,只是他在适应这个缓慢的过程。村里的白事儿积极分子又去了六顺家,这次我没敢进去,只是站在大门口往里看,有人拿席子往六顺身上卷,还说了声,都懒死了,还有心思下象棋。我一愣,然后一下冲了进去,看到那天自己握手言欢的和局被人动过了,最后的局面是红棋将死了绿棋。直到很多年后,我始终不理解,为什么六顺会因为妈妈的离开,而受到如此极端的重创,并选择在屋子里一动不动,了此一生。整个村子也没有人能理解,所以大家只能说,他是懒死的。一直有人在对我们说,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完全过不去的坎儿,他们说时间治愈一切,时间改变一切,可是总有时间和新欢解决不了的终极难题,比如一个认定自己此生挚爱只有一次的人,却偏偏失去了唯一的挚爱。后来我总是梦见六顺留下来的那盘棋,它像是心头刺一样一直在告诉我一个血淋淋的真相——所有的和局,是自己对自己的放过;所有的死局,是自己对自己的逼迫。我们要的,是支撑自己好好活下去的和局,而一根筋的人,要的却是非生即死。-END-作者
初小轨编辑
澈言主编
澈言监制
水格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