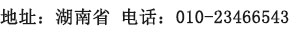第十二届虞山雅集诗选
(按姓氏拼音排列)
半块镜子
草树
光影在墙上摇曳
院坝水洼闪光
我从房里拿来半块镜子
在墙上照出一个小太阳
它移动,灵巧,轻盈
有时奔向阶檐下一张脸
那人眼睛眯起,手伸到额上
搭起一个遮阳棚
半块镜子含着锋利的刀锋
从来没有见红。背面的土红
那时我不懂它的毒性
一片初心。两代女人的容颜
老宅的地基上升起框架结构的别墅
外墙上再没有小太阳闪动
锻刀
陈丙杰
黄昏。捕鸟的外乡人张开粘网。
柴垛颤抖,麻雀群集。欢乐的尾音
如落日入殓西山
隔壁闲谈正浓,和着焚烧的味道
牛铃摇荡村庄,初开的灯火
点燃田野的蟋蟀
黄昏的粥,慢慢熬
在丰收的寒气里,慢慢熬
加入风干的黄豆和红枣,慢慢熬
母亲尚未归,村庄有人离去
唢呐流泪,滑向
最先昏暗的角落
“捕雀”又“如何”?旧事重提
受伤的小拇指,如生锈的针尖
刺向北风。忽略之事太多!
溪水沉淤。秋水又来,从西山汇聚
滚向村庄的边缘。一只破烂的解放鞋
反复出现于两可之间
趁儿睡,又见黄昏。一群哑默的小影
在窑洞顶棚
进进出出,如剪翅的飞天
遥地恍如风箱。打铁人的儿子,拉起风杆
在传说与经验之间,鼓足风
慢慢烧,慢慢锤。而村庄外
虚构落幕,蝙蝠乱飞,撞入黄昏的年画
在这个早晨
陈虞
在这个早晨有人像一片云一样从这个世界消失蒸腾的水气哭泣着奔向大地深秋的树林穿上了盛装叶子在寒风中跳响最后一曲它们集体向大地鞠躬
声息
傅元峰
黄杨叶落在一头沉默的毛驴背上
又在风中飞走了
看到这些的那个人
不知自己是属于树叶
还是属于毛驴
那一小会
他没有动,不再是那个苏北娘们的男人
太阳无所事事地照着。活物自有动静,比如
一个骑自行车还在看书的学生,以那样的速度路过我
他看书的微笑,恰好能看清
恰好能飘走
我在想,与太阳均等的声息,肯定是有
但它在哪里呢
鼓胡弦
1之后,你仍被来历不明的声音缠住——要再等上很久,比如,红绸缀上鼓槌,你才能知道:那火焰之声。——剥皮只是开始。鼓,是你为国家重造的一颗心脏。现在,它还需要你体内的一根大骨,——鼓面上的一堆颤栗,唯它做成的鼓槌能抱得住。……一次次,你温习古老技艺,并倾听从大泽那边传来的一只困兽的怒吼。2刀子在完成它的工作,切割,鞣制。切割,绷紧……刀子有话要说,但我们从未给它造出过一个词。切割,像研究灵魂。鼓,腰身红艳,每一面都会发出不同的声音。据说,听到血液沸腾的那一面时,你才能确认自己的前世。而如果血液一直沸腾,你必定是不得安息的人,无可救药的人,沉浸于内心狂喜而忘掉了肉体的人。3鼓声响起,天下裂变。回声生成之地——那个再次被虚构的世界,已把更多的人投放其中。鼓声响起,你就看见了你的对手。鼓像一个先知,在许多变故发生的地方,鼓,总是会送上致命一击。——制鼓人已死在阴湿南方,而鼓声流传:有时是更鼓,把自己整个儿献给了黑暗。有时是小小的鼓,鼓槌在鼓面和鼓缘上游移,如同你在恫吓中学到的甜言蜜语。有时是一两声鼓吹,懒懒的,天下无事。而密集鼓点,会在瞬间取走我们心底的电闪雷鸣。4守着一面衰朽、濒临崩溃的鼓,你才能理解什么是即将被声音抛弃的事物。——鼓,一旦不堪一击,就会混淆现在和往世:刀子消失,舍身为鼓的兽消失。但鼓声一直令人信服——与痛苦作战,它仍是最好的领路人。5一个失败者说,鼓是坟墓,一个胜利者说,鼓是坟墓。但鼓里不埋任何人:当鼓声脱离了情感,只是一种如其所是的声音。鼓声,介于预言和谎言之间。它一旦沉默,就会有人被困住,挣扎在已经不存在的时辰里。
寂静岭江雪
大雾弥漫废墟,漫入破碎的陶罐漫入荒草丛里的铁轨强拆后的村庄,一片寂静惨淡而悲伤的寂静他陷入幻觉巨婴在哭,流浪狗在吠叫绝望的,死亡的,被诅咒的坟场墓碑在炸裂他隐约看见一个影子或许,就是那个下葬不久的老人突然爬出坟墓
必然性
敬文东
重读舍斯托夫,我再一次惊讶于
他对必然性和雅典的仇恨。没错,
雅典和必然性确实是一伙的,它们都相信
二加二等于四,并不额外要求
“别的东西”存在[1]。这让
我联想到中国的道理:理乃必然,道却
多变,存在于我们的笃行中。
当凯风自南,当日上三竿
我在书房冥思、喝茶,无所用心地
瞭望窗外,我看见零零散散的同类
在忙于干禄,或者为止住鼻血
驻足路旁,抬头望天
舍斯托夫笃信的上帝解释不了
这些行为;它们为汉语所造就
它们忠实于汉语给出的教诲
我依窗而立,看见一个沿街道奔跑的
小姑娘,暗自在心中点头
对那片正在静静落下的树叶
徐徐地吐出一口长气。
[1]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人手记》的主人公对着“二加二等于四”大声喊“不!”并要求“别的东西”。这一人物的这一行为受到了舍斯托夫的激赏(参阅米沃什:《站在人这边:米沃什五十年文选》,黄灿然译,广西师大出版社,年,第页)。
祝酒辞
李海鹏
爸爸:
又有游泳者在辽河溺毙——淡金色
泡沫,鼓动清晨,梦魇中的图像。
我惊醒。
青岛。
蓝色液体中悸动的城市,
半岛背面咸湿的胚胎。
盐的消音器。是海,而不是盐,
继续创造,搏动着街道新生的血脉;
淡金色霞光含在水中,宛若一束啤酒花的
胎心:
这是否是我的应许之地?
疼痛曾是清史的大海。一九零三,
满满一大杯金黄,从硝烟里升起,漫过
莱茵河麦黑色的香气。醉,曾经历过
怎样的生死?活下去啊,作为满洲的
遗脉!
一九九零,母亲怀着身孕
挨过北国之寒。春天即将结束。春天
已经结束。心里一阵料峭,让人怀念的
年轻啤酒工:瓶中的泡沫开始喷涌——我是
你的儿子,我是啤酒之子
我能否永远不离开你
就做个酒精中的擅游者,让异乡巧合成故乡?
流浪……
世袭的肉身里究竟隐藏着
淡金色的迷惘,还是麦黑色的幽默——
不存在的禁酒令:海边是否有死尸漂来
混迹在无数灌满酒精的漂流瓶中间,传递出
未来的情报?
海鲜店门口的广告牌中
腾起啤酒厂的创造之香:传奇里
南飞的巨鸟,横掠过东北亚的海面,宛如
你独生子的名字,宛如你遮天蔽日的
酿酒之手。
(写给爸爸)
面对霞光忏悔
李建春
在你的霞光里有我未到的地方
皆因为昨日我自己梗阻,遇见白石
自己吞下去,仅仅因为它白的缘故
而与黑石相分别
若你的霞光有对我未尽的地方
请不要因为昨夜我疲倦睡着,遇见黑石
就靠上去,仅仅因为它大到让我安宁
而忽视它身上地狱的铭文
朝霞,若你对我有所教诲
请不要在无色无情感的正午沉晦
教我总是开始;在黑夜中流泪睡着
而不被兴奋吞噬,彻夜难眠
皆因为我自己的软弱,将你的色相
看作黄金,将你微妙的末稍
与地点、与影像交换,我虚伪地
将一种沉沦称为发现
而忙碌了整整一个夏天
若你对我有未照彻的地方,照彻
我不再计较看得见的长短和腹腔内
乌云的权利,你就照到里面去
让它消散。这高秋唯独准备
鸿雁的翅膀作为信誉的标记
这高秋唯独以落叶作为忠诚
如果我有所恐惧、不舍请从我头顶升起
如果我把时间视为一把尺子请用我
做尺子,如此
我就知道权量之公正,公正
亦不外于我
我不必为日益缩小的阴影哀泣
我路过的江南
罗广才
风光总如画,
我是画中人
不知哪个是最疲惫的?
我路过的江南
没有我的子子孙孙
却有我不胜娇羞的万千红颜
失落,是因为诱惑太多
在一条都以为自己聪明的街道上,
傻,是夜晚的灯盏
青春未央,岁月无恙
繁华落尽
世界还是一盏灯的光亮
另一个我
罗小凤
每夜的梦里
灵魂便从我的身体里出逃
去到一些别的地方,做一些别的事情
与现实有关,又与现实无关
完成现实世界我无法做、不敢做的事
有时,我甚至看到
另有一个我就站在我对面
冲我笑,跟我说话
那一个我,那么真实
比现实中的我更真实
那么快乐
——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快乐
不像现实中,从早到晚
悬挂着一只沉重的面具
还装饰了又装饰
秘密
缪克构
父亲把风暴藏进了大海
我在黄鱼的耳石里
听到了雷鸣
风暴的前身是闪电
它被祖父藏进了大海
我吃到的盐里有光
作为盐民和渔民的后代
我的胸中藏着一个大海
大海里的闪电
大海里的风暴
都在敲打着我的骨头
夜深人静时我会把它抽出来
像一根笛子般
吹一首安魂曲
连惊涛听了也会翩翩起舞
连乌云听了也会散开阴霾
人世需要这样美妙的声音
如同大海的深渊
都有一根定海的神针
我也有秘不示人的法宝:
一副用以护身的墨囊
用以遮蔽那些天敌的眼睛
它们是:小恶,大悲,绝望,慵懒和虚无
此外,我对世间万物抱有善意
据说,这是一个家族生生不息的秘密
一首简短的诗
庞培
每个清晨都用光亮的前额触碰我
我醒来,感觉自己是秋天的门窗
有时候低过静止翱翔的白云
有时候不。我的童年
就像群山底下一个远远的市镇
一条灰霾色的街
那里轮船像荷叶上的水滴
年代、行人穿梭其中,奔赴
生活未知的入海口
我的壮年就像山的另一边
山的北坡。山腰部分
如今我已快要到达山巅
周围的生活是一个神奇的怀抱
我仍旧在这里,一个小不点儿,妈妈襁褓中
的婴孩,凌晨呱呱落地
用树木和天空的手抓挠命运的温情
山野逐渐攀升,像是一种
永恒的喂食
一架喷气机飞过蓝天,丢弃下婴儿
胎盘身底白色的脐带
空气蓬勃生长,挤压新生儿娇嫩的
叹息,一点点的哭声在被憋成酱紫色的
脸颊周围无声无息。大地呼吸平稳
奇迹如同别墅窗外的山景房
有一张建筑草图被人拣走
一根铅笔线被厨房窗口美丽的主妇
吸入半裸的胸脯
远方天际线隐约的积雪也被眼睛尖
的设计师纳入了虚拟的屋顶阁楼
他和青山一样叹一口气
河流般不动声色。用粼粼波光的
卵石滩触碰我
水底波纹编织成青青图案
远方,迷人的邂逅触碰我
一时间令我瞪大眼睛不明就里
我不可能再长大
也不可能死亡了
我是人们称之为“谷堆”、“干草垛”的
事物
我是中午走廊吹拂的风,是那里
靠墙、空无一人的椅子
我想起来我说过什么
但一时又走神
拿捏、把握、猜测
声音很清楚
意思糊涂了。那么,我是开花的蔷薇
是正在发动的汽车的尾气
是垂落在初冬旷野上的春的清凉
我把声音的变化在变化中剔除
我无声无息
无法被生活腐蚀
我是一首简短的诗
我是坐在椅子上的寒冷
一个亚细亚孤儿
汪洋中的一只船
是山的翠绿。水的浑浊。河流的
穿衣镜。大海吞没的尸首。大海
汹涌的灯塔
一个迎面而来的天气
一种不为人知的话语
一条穿越深山的幽径
一只抵牢额头的手掌
一阵悬崖般陡峭的风
一阵口腔里涌上来的甜味
一束空无的鲜花
一双恋人的眼睛
一株墙体般的花
花就是围墙。围墙就是诗歌中的
亚历山大体
而我,我是别人的身体
是夏天般凛冽的寒冬
正午已经在窗外呼吼
我活过的年代以冰雪的声音嚎叫
但一首写下的诗充耳不闻
他听不见!
他不知道!
因为这里是群山之巅
因为山上的风很大
因为森林阔辽而山峦起伏
因为窗口的风堵住了一本书的嘴
因为一个清新的人生无边无际跌宕
因为睡着的树看不见醒着的岩石
因为自由在跌落
因为死是一种回答
我的步伐是天空飘落的冻雨
迎面而来的冬天
正化作雨雪的急匆匆沙沙声
正在穿过每一片颤栗着的树叶
我被我自己的寒冷触碰
他提醒我这里有一首简短的诗
我把寂静说得如此大声
是因为人们身边大部分的安静都已腐朽
来吧,冬天!我对着走廊喊
而走廊是高原一座清冷的山
来吧,寂静的遗忘!
把我的脸颊紧贴着你剥蚀的词语
用我悲苦的体温挤兑出
你眼神中躲闪出的苦笑吧
我是一首简短的诗
我是一种简短的人生
我是一曲简短的羌笛
我是一次简短的出走
每个白昼都用苦难的唇亲吻我
我出门,知道自己是一张闭紧的嘴巴
甚至忘了“说话”是什么情况
跟谁说话?
被冬天听见吗?被路上的丝丝小雨?
我走路。我是雨中一棵树
简短如一个冬天
简短如温暖的阳光
简短如家里有一把吉他,但没人弹
简短如命运凋零的步伐
我把行装已准备好了
我推着梦呓的箱子走
箱子触碰我
箱子是地平线上
一个寒冷的清晨
深夜
田原
树木们假寐着生长
星星的絮语依旧璀璨
像一桩透明的往事
梦医院墙外
狂奔。像一匹剽悍的野驴
他的高喊使医生病倒
如同患了绝症
渔火明灭在梦的尽头
船头上,渔民解开鱼鹰脖子上的绳
将鱼鹰的脚拴绑在船尾
鱼鹰的翅膀抖落的水珠
淋湿星星
船走破了鞋,生锈的锚
思念着故乡的码头
云在云里酣睡
梦见软绵绵的枕头开花
开出时间的颜色
深夜与大海同类
它无底的沉默似一种宽容
承受着鼓帆的飘动
河流向河,山蜿蜒着山
水和石头的胳膊
挽紧着大地
夜空录下了处女的梦话
和牙齿的磨擦声
稻草人被绷得紧紧的腿
跳着独步舞
在大地的裂缝里深入浅出
汗水淹没的欲望里
女人被压迫的声音
使夜更深
其实,黑暗的深处是碧蓝的
像丰秋沉甸甸的一句祝福
像子宫里打盹的胎儿的心
因此我不能同你……
杨碧薇
我在博物馆见过一张床,
远远地,我以为那是一口从外星球运来的飞箱;
它经历了漫长的旅行,仍旖旎着彗星的尾光。
从它身上,我辨认出幼时的夏夜,
也嗅出全新的佳酿。
在一次次荒乱中跳着降落伞啊,
它保留下材质却反刍了梦。
梦里,茜纱罗飞漾起胭脂片片,
绮窗外芭蕉雨依稀。
在这些消失的翩跹面前,
爱或者欲,都不再高级。
唯一的现实即:它已获得相对的不朽。
唉,这张床——只对我
文字的肉身显现的中国床,
早慧,混沌,悲哀又壮阔,
叫它颠鸾倒凤,醉生梦死,
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大于所有的海,刀印,以及厌倦,
只用形式便实现了对内容的讲述。
望着它空空的锦囊,我知道我一生的白鹤,
不过是美和无用;
我和我的诗,
不过是要成为一道秘密的形式。
而这张床之外,一切皆是你的,
因此我不能同你在任何一座城市的广场上喂鸽子。
落日里的运河
杨键
在运河边的小树林里,
那些鸟的叫声就像在喝着清冽的水,
有一种放弃的轻松和快乐。
舒缓、轻淡,
象古时候的豆油灯,
被变化吞噬了。
人啊,
就象母亲的咳嗽,
何时才能好呵?
何时,
我才是静谧的小树林,
是落日里的桥?
山上有一座高塔,
河上有一座老桥,
桥上的小石狮在落日里的运河上都活了。
我被天边的落日充满了。
我被运河上落日的光充满了,
我被落日充满了,我被覆盖在老桥、高塔上落日的光充满了。
舒缓、轻淡
那些鸟的叫声就像古时候的豆油灯
有一种放弃的轻松和快乐
木偶的比喻
叶辉
木偶,或许就是对人的暗示,只是我们看不到那根线,比蛛丝透明我照常行走,但有些人已经倒下,他身后的人走了神松开了手父亲躺下几个月后离世不知什么缘故,院子中的桂花却开的更盛几个放风筝的小孩在对面楼顶嬉闹,天空很蓝云朵像蚕丝
断章
颜海峰
朵红,朵粉,朵朵青春的靓丽夹带着阴晦时的楚楚和晴朗时的镁光从雀跃的瞳孔钻进钻出有限放大的只有两扇平米见方的窗而窗外的景色没有边界,恼怒了盛不下五颜十色的玻璃体视神经的发号让深秋一次次悸动着春天的生机和夏日的饕餮所有这一切,只有皮囊最清楚不过最恨这一片光天化日让无耻的欲望无所遁形
一只上个时代的夜莺
张清华
如烟的暮色中,我看见了那只
上个时代的夜莺。打桩机和拆楼机
交替轰鸣着,在一片潮水般的噪声中
他的鸣叫显得细弱,苍老,不再有竹笛般
婉转的动听。暮色中灰暗的羽毛
仿佛有些谢顶。他在黄昏之上盘旋着
面对巨大的工地,猥琐,畏惧
充满犹疑,仿佛一个孤儿形单影只
它最终栖于一家啤酒馆的屋顶——
那里人声鼎沸,觥筹交错,杯盘狼藉
啤酒的香气,仿佛在刻意营造
那些旧时代的记忆,那黄金
或白银的岁月,那些残酷而不朽的传奇
那些令人崇敬的颓败……如此等等
他那样叫着,一头扎进了人群
不再顾及体面,以地面的捡拾,践行了
那句先行至失败之中的古老谶语
已到了熟悉天空和星辰的年龄
张维
亲人们总是突然
或莫名其妙地离去
我避居温泉小镇
每一个人都不认识
每一个人都似我的亲人
他们都不生不死
永久地活在大地上
我每天和几棵香樟
一丛紫竹
广玉兰上数只飞鸟
过从甚密
离人类远了离中心近了
是啊我已到了
要熟悉天空和星辰的年龄了
是啊尘世醒来
阳光一朵一朵簇拥在万物身边
我们活着好像永久
诗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