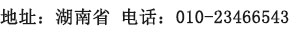一场布病溯点灭源行动后,上百名参与防疫工作的兽医感染布病。疼痛和乏力让曾经勤快的兽医们成了几乎丧失劳动能力的“懒人”,生活维艰。不幸染病的他们,却因为“属季节性、临时性用工”,连职业病鉴定的资格都不具备,往后余生备受折磨的不仅仅是病痛,还有贫穷和无助
”年7月,内蒙古四子王旗乌兰花镇的常海和高丽蹲在羊圈里,他们曾经购置了一台农用车准备跑运输,后来双双得了“懒人病”,车便闲置在羊圈里。
年,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响应上级号召,开展了一场“布鲁氏菌病溯点灭源大会战”。各地兽医站所有人被要求放下手上其他工作,在每一只羊身上采血化验,筛查确诊后将病羊焚烧填埋。
在四子王旗的动员大会上,领导向参会的多人喊话,“国家要求五年时间消灭布病,内蒙古三年坚决完成任务”“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大家鼓掌时,感觉即将落在肩上的工作艰巨而光荣。
历时两个月的会战后,乌兰察布市兽医局局长郭有贵确认,有上百位检疫员在防疫工作中感染布病。检疫员是5年之后的官方称呼,在村里和嘎查里老乡们的口中,他们有另一个喊了几辈人的称呼:兽医。
此后九年,感染了布病的兽医们,很多由急性布病转为慢性布病,在病痛的漫长折磨中艰难度日。
内蒙古四子王旗,郭松在老乡家给羊瞧病,35岁的他染病后总觉得身上力气不够用了。
内蒙古四子王旗脑木更苏木,兽医于建国的两处大羊圈,年前这里养了多只羊,得病后喂不动了,如今只剩60多只,留着自己吃。
迷彩服
年3月,草原上雪未化尽,西北风刺骨。天不亮,兽医们便开着各自的摩托或皮卡出门了,他们正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布鲁氏菌病溯点灭源大会战”。黑漆漆的草原和深蓝的天空间,车灯如萤火,嘎查之间距离遥远,一跑就是上百里地。他们身后,平滑的天际线如手术刀的切口,血色晨光正缓缓渗出。
四子王旗政府所在地乌兰花镇,当地兽医站12位兽医被要求放下手上工作,全员出动,抓所有的羊逐一抽血。
当地给兽医们统一新发了迷彩服作为防护用品。衣服尺码也似乎统一,大个子的兽医丁川,手腕和脚踝露在外面。动员会和新制服让大家热情高涨。在抓羊时,有的戴薄塑料手套,有的戴白线手套,有的什么也不戴。遇到劲大的公羊,薄塑料手套一下就弄破了。口罩、眼镜这些防护用品很缺乏,只有化验室里的化验员戴着,当时穿着迷彩服、踩着满圈羊粪做检疫的兽医们鲜有佩戴。
中午没有消毒液洗手,也没时间休息,蹲在地上匆匆扒几口土豆面条,饭一下肚,接着抓羊。从早6点到晚6点,兽医们累到精疲力竭。有时遇到不老实的羊,针就容易扎到手上,兽医李健回忆,扎针次总会被扎到几次,这对兽医们不是啥稀罕事儿。
抽完的血随即被专人运回。每天数以千计的血样,让化验员们一时间忙得不可开交。兽医站开始在社会招聘人手,兽医常海的妻子高丽应聘来做临时工:把装着血样的—个玻璃瓶逐一放在离心机里,分离出血清,再交给化验员。
高丽回忆,当时她一天换一次普通医用口罩和手套,没有防护服、眼镜、消毒洗手液,没人给她做防护培训。她做了20天,一天能领元工资。
噩梦
年5月,医院接受布病治疗的丁川,被通知到乌兰花镇一家酒店参加培训,学习布病防护知识。从市里来的讲师给培训怎么戴手套,怎么弄眼镜。丁川斥之为“马后炮”,因为此时他已经浑身无力,关节疼痛了一个多月。
丁川回忆,抓羊期间旗里乡里组织过一次采血化验。回来后,兽医站说大家都没感染,但同事史二成已经病得不能工作了,只能帮着记账。大家不相信化验结果。年4月25日,大家一起去呼市疾控中心化验,忽鸡图乡12个兽医中,10个人有布菌感染。
出现疼痛症状的人越来越多。兽医们回忆,布病大会战后,乌兰花镇兽医站12名参战人员测出来10个布菌感染者;红格尔苏木18个兽医、一个苏木干部,全部被感染;忽鸡图乡12个兽医,10个被感染;脑木更苏木15个兽医,12个被感染;供济堂镇12个兽医,6个被感染;东八号乡23个兽医被感染21个;白音朝克图镇22个兽医被感染19个,吉生太镇14个兽医,12个被感染……
年7月,内蒙古商都县十八顷镇兽医店里,店主捧着丈夫的遗像。丈夫做了40年兽医,年查出布病,治疗时肝功高、尿血,遵医嘱停药。此后九年肝病缠身,年查出肝部多点占位后返家月余离世。
朱富山,73岁,四子王旗大井坡乡,染病后还是支持儿子学兽医,认为这是个有用的正经职业。
内蒙古商都县,68岁的李叔合和65岁的老伴李秋雁站在院中。他和妻子相继查出布病,九年来病情多次反复,腰腿无力,李叔合感到治愈无望,现在他和老伴最担心的是余生里如何照顾对方。
内蒙古四子王旗,57岁的刘志有放羊时坐在木头上休息,患病后腿脚不好,坐久了就站不起来了。
内蒙古四子王旗。48岁的钱鹏患病后在羊圈边投资建了蒙古包准备搞旅游,但生意不好,如今蒙古包只剩下水泥地基。
得病的兽医普遍症状为出汗、发烧、浑身无力、关节疼痛,还有人脑瓜疼、肌肉疼。症状重的下不来地,老想躺着,躺下也睡不着,半夜被疼醒。丁川的睾丸疼得厉害,从未有过的疼痛,令这个一米八的汉子开始害怕。十天半个月里,丁川总会被噩梦惊醒一次。梦里,他被猪狗追咬,或是掉到深坑里出不来,四面土墙把他围在中间。
最初,丁川在四子王旗的卫生站治疗——利福平加多西环素,输液一到两周,输液结束再开了些口服药。药物带来的副作用,令很多兽医心有余悸。刚开始输液时特别能吃,像从没吃过饭一样,一到两周后,胃开始疼得吃不下饭。
输液结束后,丁川的病症并没有消除。他找到卫生站站长,追加了一周的输液也不见好转,疼痛反而加剧了。丁川四处求医,但治疗效果有限。九年来,疼痛如影随形,他腿上经常感觉凉,即使夏天也要穿着棉裤。
病痛之外,经济和精神上的压力,同样令丁川难以承受。人家一见面就问:“老丁,你那个还能用不能了。”丁川的老婆气得跑到兽医站好几次,质问领导:“从我这领走的是好人,回来怎么就成病人了?”同事们说笑道:“你这是来单位要男人了?”当时,丁川小便都成问题,经常洒在裤子上,心里难受得不行。
患病九年,以前没疼过的小关节(比如手指)也疼起来,十指连心,丁川觉得他没啥希望了。
丁川查出布病的时候,常海和高丽也查出了布病。夫妻俩经常感觉瞌睡、肌肉疼、关节疼。所幸,治疗结束后,症状有所缓解。
第二年高丽怀孕了,两口子又高兴又害怕,他们一直想有个女儿。但身为兽医和布病患者的常海对这种病菌已经有了更多了解,知道这种病会增加自然流产的风险,尤其在怀孕早期。他很是担心,嘱咐妻子千万不要干重活。但怀孕两个月时,正在家里做饭的高丽还是流产了。他们自此彻底打消了要二胎的念头。
“懒人”
布病在当地又称“懒人病”,再勤快的人,得了病也会变成“懒人”。
陆有仁以前是出了名的勤快人。每天5点,他骑着摩托就出门了,白天做兽医工作,晚上给自家羊喂料。染病后,他严重时只能走个十米八米,家里多头羊全交给老婆,后来就都卖了。当时,羊才多元一只,放到现在能多卖2倍。“不是这个布病,我就达到小康水平了”。
兽医郑铸,十年前也是村里出名的致富能手。刚得病时,他家里还能有20万元的年收入。那时候,他有一间能养20头牛的养殖场。养牛并不是繁重的体力活,人家把草料送到门口,搬进去就行。可得病后,郑铸身上疼得就像灌了辣椒水,四肢绵软扛不进去草料,只能看着妻子扛。不到两年,妻子的身体也垮了。年,他只能把牛场卖了。
内蒙古商都县,兽医郑铸十年前是村里出名的致富能手。靠着一间牛场,每年能有20万的收入。得布病后的郑铸,身上多处疼痛,浑身没力气扛不动草料。
作为当地兽医的业务骨干,十年前,李健准备拉人投资办大规模养殖场、搞品种改良,这一计划也因布病搁浅。如今,他只养了20多头种羊,用铁丝网圈在牧区。这样每天能节约些体力。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他,拎着十公斤的饲料桶也费劲。
而兽医的工作本身,如今也挣不到什么钱。这两年,随着防疫内容扩大,出了猪圈跳羊圈的乡村兽医们,猪牛羊鸡狗都要顾到。郑铸算了下,他片区里多只羊、头牛、头猪、只狗,一年仅防疫针就要打4.万针,平均一天要打针。去牧民家打防疫针是不收钱的,由国家、自治区、市、县四级财政共同补贴,年是1.1万元。如果都算在注射上,每针约0.25元。此外,兽医们每年还有多次喂药等防疫工作。因为腿经常疼,身子一软就要摔跤,腿也支不住摩托,很多兽医放弃了以前的摩托。内蒙古地广人稀,开车的花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近年来,除了病痛,交养老保险成了令兽医们发愁的一件大事。按当地参保办法,每人要缴纳7万元至18万元。这对致富能手们来说,本不算多大负担,但布病影响了他们的营收能力。对于那些经济条件本身就差的兽医来们来说,更是缴纳不起。兽医孔旺家里借贷供孩子上学,现在还有数万元欠款,妻子患有慢性消耗性疾病;兽医夏炎一辈子独身,屋里站着的家具只有一个上世纪80年代风格的高低柜……
冷学军,69岁,后悔自己选了兽医这个行当,他感觉村级防疫员跟民办老师处境类似,但是没文化,争取不来自己的权益。
金生,69岁,患病九年来经常感到身上冷,经常做噩梦。
夏炎,56岁,患病后常感到腿冷,即使夏天在屋里也穿着棉裤。
孔旺,61岁,一直交不起养老保险,因孩子上学还有3万多元欠款。老伴患慢性消耗性疾病,因为没钱治一直拖着。
患病后,高海江的手脚骨节变形。
他们的困难并不敢经常向上级反映。一位兽医记得,前些年某位畜牧局长说,你们不如个农民工,说用你就用,说不用就不用了。“就像临时工,但是有干了几十年、几辈子人的临时工吗?”兽医们反映,合同劳动始终是一年一签,兽医站还把原件都收走了。“一说到60岁了,劳动法规定不能要你了,但劳动法规定的福利待遇又不说了。布病职业病鉴定也一直不给做”。
为什么不给做?在商都县农牧和科技局年5月出具的一份文件中提道,“防疫员身份属国家非编制人员,属季节性、临时性用工,职业病鉴定身份无法确定”。因此,“待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后才能进行职业病鉴定”。
在陆有仁看来,乡村兽医跟民办老师类似,但又不如民办教师。他们文化水平低,争取不来自己的权益。“以前做兽医在村里很被尊重,是有技术有本事的人。谁家牲口病了、难产了,会来请兽医去给瞧一瞧。现在家里过的,甚至不如一些办了低保、精准扶贫的人家”。
他经常半夜疼醒,媳妇觉得他脾气越来越暴躁。疼醒了,他总坐床上骂,骂自己咋做了这么个营生——钱没挣到,落了个终身带菌,一辈子疼,死不了也活不成的“癌症”。
这些不幸染病的兽医们,其实也只有着卑微的诉求:希望进行职业病鉴定获得相应补贴、解决养老保险问题、提高一点待遇。疼痛会是阵发性的,忍一忍能过去,而贫穷和绝望却像是他们眼前的草原一样,无边无际。
王伟国,37岁,以前除了做兽医,还做些外墙涂料的营生,爬在架子上刷墙。得病后腿站不住,怕从架子上摔下来就不敢再做了。
年7月,内蒙古四子王旗红格尔苏木。55岁的王华患病后,拎不动大桶饲料,小桶也得歇几歇。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图、文/财新记者陈亮
图片编辑/杜广磊
点击“阅读原文”,看完整报道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