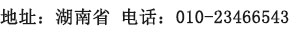山东白癜风医院 https://m-mip.39.net/nk/mipso_4337492.html
羊倌房子
我们生产队有一块“飞地”,就是一块明明属于我们的土地,却被一条深沟大壑与我们西营子梁隔开,反倒和北边另一个生产队的土地相连,这就给我们带来极大的麻烦。单说春种秋收,开春,那大几十亩的土地耕种,总得粪土吧,就得人们用队上的驴骡牛马套了小板车,往那儿送,一车,又一车,出村,向北,绕过西北的大梁峁,再转回来,才到,一天跑不了两回。秋后,收割了,同样,用驴骡牛马车往回拉,一车,又一车。真是费时又费工!为此,队上的几任队长,都想与北边那个生产队协商调地,就是用我们的那块一等好地,置换他们与我们生产队相连的一块三等瘠地,却一直好事难成。那年,赵四当了生产队长。一天劳动歇息时,他蹲在高高的沟崖畔,伸着脖子,眺望着隔沟那块虽近在眼前,却望地跑死马的田地,手指夹着的自卷烟,一棒完了又接一棒。待第三棒烟丢开,他往地上稠稠儿吐了一口,呼地立起,掏出家具,向北边那个生产队,猛猛的撒一道尿,就尿就骂:还整天说甚么人民公社是一家呢,球扯淡,别的人尿你,你赵四爷爷才不尿你狗日的们呢!第二天,赵四就带了队里的精壮劳力,由几挂车拉了工具材料,浩浩荡荡开到那块土地。靠沟畔选了一块地方,开工夯土筑墙,没用三天,就围起了两个无顶的羊圈,边上再加盖了一间有顶的房子。一切就绪后,赵四就开会下令:生产队所有的四群羊、四个羊倌,夏秋两季,每月轮流去那里过夜,每班两群羊两个羊倌。这羊屙尿下的不就是粪吗?这办法,谁也不敢说不好,把往年最让人们头疼的送粪问题,一下就解决了。可羊倌们却要辛苦了,起码,这一夏一秋,他们好些日子就不能回家啦,就得到那里过夜攒粪,那里也就随之有了一个新的名称:羊倌房子。我的父亲就是生产队四个羊倌之一。那时,我们是五年制小学,不是全日制,每天只上半天课,放学回家,下半天还要帮着家里干活。由于父亲是羊倌,我每天下学回家,一放下饭碗,就得提起饭罐,去给在村外山野放羊的父亲送饭。饭往哪里送?父亲的羊群在哪儿,饭就送到哪儿。说是送饭,有时就成了放羊。一个十二三岁的娃独立放不了一群羊,父亲就让我们混群,就是和另外一个羊群混合起来放,由我给另外一个羊倌搭伴子“拦坡”。在我们那地方,领羊出圈叫出坡;放羊在坡上,不让羊乱跑,叫盯坡;追羊乱跑,在坡地上拦着,则为拦坡。而父亲呢,则偷跑回家,侍弄家里那点自留地去了。通常,我是与天星叔混群。天星叔是个大个子,二十六七了,还没对象,父亲已为他跑了不少腿。虽还是没结果,可他俩在生产队的羊倌中,关系最好。父亲让我一个娃娃,与别人混群放羊,恐怕也只有天星叔才会心甘情愿。我们那地方,虽已是塞外,还属黄土高原,是半农半牧区,放牧的草场窄逼,所以羊群一般都不大,最大也不超过一百只。混群放羊,只能在村外的荒山野沟。两群羊合二为一,羊群大了,还不是主要问题,混群最大的问题在头羊,羊群走路靠头羊,每群羊都有一只头羊。头羊在羊群里有绝对的权威,每天羊出坡,是它第一个迈出羊圈门,天黑,羊回圈,也是它第一个进圈。在山野田头,头羊永远是走在羊群的最前边。只有在一些开阔的地方,羊群散开吃草时,头羊才暂时混同于一般羊。一句话,头羊的权威,可以说是在羊倌一人之下,百羊之上。混群的问题,就是两个头羊的问题,往往不好处,就像两个单位的“一把手”。官级一样,在一起做事,谁也不服谁,肯定尿不在一个壶里。所以,羊群混群的情况一般不多。我与天星叔混群放羊,当然是因为父亲的缘故。好在天星叔愿意。慢慢地,父亲那群羊的头羊碰到这种时候,倒也懂事,自觉屈居第二。故,天星叔掌管羊群全局,我则拿了父亲的羊鞭,在羊群前后左右跑来奔去。配合得倒也……还行。那天,正好又轮到天星叔与父亲的羊群到羊倌房子过夜。第二天又是礼拜天,不用上学,送饭到羊群饮水卧晌的西沟河滩上,我就对父亲表态:大,你吃了饭就回吧,我跟天星叔混群呀!这天一后晌,想到晚上就要与天星叔两个人,住到那羊倌房子,就很兴奋,有点等不及天黑。太阳终于落到西边黑黝黝的连山后边去了,天上出了星宿。天星叔吆喝着头羊,往他还不习惯的北边梁上的羊倌房子走。羊群里的羊们也不大习惯。圈好羊,天星叔用一把很大的钥匙,开了小屋门上的锁。他先进去,用火柴点亮了挂在墙上的玻璃罩马灯,才转身对一直站在门槛处的我说:进来了哇!房子不大,门窗几乎相连,都是从什么地方拆下来的旧物,里边一盘火炕,一方灶台,灶台边的地角置一口黑瓷大瓮,灶口上有一口小铁锅,炕角还有一个油渍斑斑的木头箱。天星叔拍拍小箱盖说:这可是咱们的百宝箱,做饭的米面油盐勺铲筷碗都在里边。天星叔叫我到门外一个墙角抱回柴火,他就揭开锅盖,吹了吹,添了水,往灶里填柴,点火,然后,打开百宝箱,一样一样取出东西,开始做饭。饭是小米焖干饭,菜呢,只一样儿,将一把干红腌菜放在碗里,舀一勺米汤泡开,就是。这顿饭,我吃到打嗝,天星叔笑着看我,说:咱这饭叫懒汉饭,也叫神仙饭。我想起一本书上说神仙可是能餐风饮露的,这些羊倌们再懒,也得吃小米饭就红腌菜,最后,还要喝一碗米汤,可见还都算不上神仙。(秦永新原创摄影作品《娄烦马》)那天,是七月中旬,白天热,晚上也热,早睡不着,到了羊倌房子外边,天上是一轮眼看就要圆了的大月亮,疏疏的星宿,把个天地照得明明白白。远近的山野好像罩在一片蓝色的烟雾下,北望有几点微微的灯火、狗叫、驴吼、娃娃哭,是另一个生产队了。乍蓦离开自己熟悉的家,来到这里,心里不知为啥,一下子还有点忧伤、凄凉。有狗叫,好像就离我们不远,天星叔说:东边崖畔下有一户刘姓人家,住窑洞的,肯定是他们家的狗。回到屋里,扯开炕角的两套破铺盖,在席片上铺开,睡下,天星叔光着身子欠起身,将墙上的马灯熄了。我却咋也睡不着,就缠着天星叔再给我讲一个故事。天星叔枕着他那高高的枕头,讲了起来,说有一个人出门,晚上住进一家车马大店,那天下雪天冷,这个人来迟了,轮到他,只能睡店里靠门窗的冷炕头,他不甘心,对同住在店里的人们说,他会讲《西游》,那些因夜长睡不着觉的人就说,那你就给咱讲嘛!这个人说,讲倒不难,只要那个睡锅头的人肯跟他换个地方,他就一定讲。恰那个占了热锅头的人,是个最爱听故事的人,二话没说,跟他换了。这个人睡到锅头,噗——噗——放了两个响屁,就开始讲:“从前,唐僧去西天取经,带了三个徒弟,其中一个,叫狗八戒……”那个让了热锅头的人连声吼:“打住……打住……”把这个人的故事打断,他大声询问住店的人们:“你们听听,他说的这是甚么鬼话?人家唐僧去西天取经,带的三个徒弟,一个孙悟空,一个沙和尚,还有一个叫猪八戒,这咋就成了个狗八戒?!”众人正七嘴八舌,这个人却说话了:“我说狗八戒就是狗八戒,你说不对,那请你来讲!”这人说完话,就一抖被子仰面大睡了。我发了一会怔,还想往下听,却听到了天星叔的呼噜声。我不由得想,那人明摆着不会讲《西游》,是在骗人,那个爱听故事的人上了当,让出了热锅头,他就这么肯罢休了吗?要是换了我……我醒来时,满窗阳光,因这窗户是朝东而开。翻身一瞅,天星叔的铺盖是空的。胡乱穿了裤子跑出去,天星叔正拿着把羊铲,将昨天羊回圈时遗在圈门外的星星点点羊粪,铲起,往羊圈内丢。由于羊群出坡,要在小晌午(约上午十时),天星叔不慌不忙,直到把羊圈门外,还有周围的每一点羊粪都弄到圈里,才在墙根蹲下来卷烟抽,抽毕两支,才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回屋拿出个搪瓷茶缸,上面印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去争取胜利”几个粗壮的红油漆字,进了羊圈。他伸手逮住一只母山羊,蹲下,将那母山羊的一条后腿提起,往自己的一条腿弯里一夹,茶缸伸到母山羊的奶头下边,另一只手开始挤奶:唰——唰——连着挤了三五只母山羊,茶缸里泛着沫子的雪白奶水,已快满了,他就端着羊奶回到小屋,和我把昨夜多焖下的小米干饭,泡着羊奶吃光,又门里门外闲走了一圈儿,才拿起羊铲,说:该出坡啦!要说,放羊也绝不是甚么轻松的营生,然而,跟着天星叔混群放羊,我倒很乐意。首先,天星叔会一天不断地给我弄一些好吃的,一个小瓜,几颗酸果,最多的还是野果、沙奶奶、锁牛牛。最不济,也有蒲公英的根茎,我那时候嘴真馋呀!再下来,就是天星叔很会讲故事,他肚子里好像装满了故事,只要他肯讲,张口就来,比如说,因为肚子饿,他就给我讲起王母娘娘与牛的故事来。他说,当初立世时,上帝要给人定规矩,天上的王母娘娘就差牛下界来传一道令,要这世上的人们:“每天一吃三打扮”。牛下到人间来,却误传成“每天三吃一打扮”。这可就坏了,害得地上的人们,一辈子为了刨闹这“三吃”,累死累活,还总是吃不饱。天星叔感叹:要不是牛传错了规矩,这世上的人,天天起来,就照着镜子打扮,只吃一顿饭就行,那该多好啊!起码,我们这些放羊的,羊出坡时吃上一顿饭,也不再用人给我们天天送晌午的饭啦。我听了,也觉得这牛真他妈的实在太笨,连传个话都传错。天星叔继续说:这笨牛上天复命,王母娘娘一听,就知道坏了大事儿,可也再没有更改的余地,一生气,抬腿一脚,把这笨牛踢了个满地找牙,还贬这笨牛下界,永世为人们干活受苦。要不这牛,为甚一生下来就都没有上牙呢?(秦永新原创摄影作品《娄烦马》)牛真的没有上牙?为此,我曾专门跑到我们生产队的饲养院,掰开那些在槽头吃草倒嚼的牛的嘴巴来看,果然,没有一个长上牙的。不过,最最让我欢喜的,还是另一件事儿:打野蜂窝。就在羊倌房子后边的一面黄土崖壁上,有一个葵花盘大的野蜂窝,一大团野蜂在那里像场面上扬起的谷壳,扬过来,扬过去的。父亲是连靠近都不让的,说:野蜂,是最惹不起不能惹的,它们会把人的脑袋蜇成个大南瓜,闹不好还会要命。可天星叔却要领我来捅这个野蜂窝了。那天晌午,父亲吃过我送来的饭又回去了,羊还在河滩的沙滩上卧晌,天星叔让我把衣裳都穿好,还用细柳条扎了袖口裤角,然后,他将我拉到有一线流水的河滩中,用河滩上的又稀又湿的细红泥,抹了我一头一脸,连手都抹了,他自个儿也如此。这下我们谁也不认识谁了。他折了两把细柳条给我,自个儿操了放羊铲来到那面黄土崖下,瞅准了那蜂窝,几下就将那野蜂窝捅得掉下来,成团的野蜂尘土般飞起。天星叔冲我喊:快打,快打。我就用两手的柳条一顿乱抽乱打,他则拾起野蜂窝跑开,我在后边追,头上、眼前,全是急了眼的野蜂,无奈它们蜇不到我们,有的就撞在了抹在我们头脸上的红泥上。按预先说好的,我跟着天星叔跳到河湾的一潭绿水中。这天黄昏回村,当父亲看见我手里抱着的一个葵花盘那么大的野蜂窝时,惊得眼珠子差点从眼眶内跌出来。野蜂蜜是真香甜啊!不过,天星叔也并不是对我就百依百顺。比如有一次,我和他站在高高黄土崖畔撒尿,我们比看谁尿得高尿得远,可比着比着,我不知咋的就要看他的鸡鸡,好像听村里的谁说过,天星可长得个大鸡鸡!这回,天星叔就不干了,他转着身子躲着我,还伸出一只手将我往远外拨拉,害得我尿在裤子上。他声色俱厉地教训我:你这娃娃,这东西能看吗?他那时好像真恼了。我也躲在一边,半天没跟他说话,他终于过来了,很认真地说:不是叔恼你,你娃娃这做法不对,记住,这东西不能看,看了三年愁!我怕他再恼了,也就似懂非懂地点头,其实,我心里却想,自己长的个东西嘛,为甚就不能看,还三年愁?天黑又到羊倌房子过夜。做饭时,天星叔突然对我说:去,去东崖畔下那家人家借半碗盐来!我知道那家人家姓刘,男人叫了个女人名,刘秀。也见过几次。我拿了碗,跑出了门。天星叔追到门外,又叮嘱:记住,再要几根葱!到了刘秀家,刘秀不在,只有他家闺女在,十八九岁,长得还行,只是两只眼睛,好像不一般大,牙却白。她听我讲明来意,二话没说,就从炕上跳下,给我去挖了多半碗盐。我再回到羊倌房子时,才想起,忘了要葱啦!就在这时,门口有人来,天星叔正一脚在地一脚踩在灶台上做饭,回头一看,忙笑着说:啊!绊女子——那女子举举手里的几根葱叶,笑笑说:没葱不行哇!那夜,我们吃的是天星叔后晌放羊时,一土坷垃打住的一只野兔。绊女子除了拿来葱,又回家寻了一回调料。她肯定地说:吃兔肉,没调料根本不行,膻腥得吃不成!兔肉做好时,天星叔请绊女子与我们一起吃,绊女子只捡了一条腿,尝了一下,就说什么也不肯再吃。天星叔还在劝,说:见吃不吃有罪呢。绊女子却说:人家最爱听你叨古今。我明白,叨古今就是讲故事,就忙咽下一口嘴里的肉,插嘴说:天星叔的故事比牛毛多,三天才讲了一个牛耳朵。可这个刘绊女,肉是不吃,故事到头来也没听成,有人在东崖畔那边喊魂一样喊她呢。刘绊女滑下炕沿,急匆匆走了。我却突然对天星叔说:你不是光棍没老婆,为甚不把这绊女子娶上呢?我话音未落,脑瓜上就着了天星叔一巴掌,还是油巴掌,天星叔瞪着眼骂我:球大个东西,甚也敢胡说,人家……人家早就有婆家了嘛!我赶紧缩头后退,嬉皮笑脸说:人家不是不知道嘛!后来到羊倌房子过夜,几乎每次总能看到那个刘绊女,她每次来都不空手,不是拿几个土豆,就是抓一把青菜,一次,还抱来一个西瓜。天星叔当然也没少给她叨古今。什么薛仁贵征西、杨六郎探母、双锁山刘金定的马蹄印、洪州城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听得我们都眼瓷了。刘绊女听完一个故事,啧啧着,用她那有些不一般大的眼盯住天星叔说:天星,你这么有文化,咋不好好念书?天星叔仰面哈哈大笑:你说我……有文化?真是失笑死个天下人呀,我连小学三年级都没念完,跟这小子还差两年级呢。??(秦永新原创摄影作品《娄烦马》)唯有一回,天星叔讲完故事,刘绊女没夸他,骂他“坏”,还扑上去,用两手在天星叔身上狠狠拧了两把。那天,天星叔讲的是这么一个故事,说:哪个大队有一个放羊的十七八岁的小子,还有一个也放羊的十五六岁的女子。两个放羊的,山坡野洼老碰见,就认得了。一次,他们晌午都到沟里水坝边饮羊卧晌。正遇上春夏之交,羊发情,两群羊里的羖羝和骚胡,忙着撵着母羊“走羔”。这小子看着看着就起身去尿。女的也跑到一边的一个小岔沟。女的尿回来,这小子又要去,也跑到那个小岔沟。小子再回来时,眉眼都变了色。女的问:咋啦?小子说:刚才……你都尿了些甚呀?女的说:尿嘛,能尿甚?不就是尿水嘛。小子一把拉起那女子,跑到她刚才尿过的沙滩,指着:你看,你自个儿看。女的一看,傻眼了,刚尿过的水渍上,有一些白花花的虫子一样的东西。这是甚呀?你有病了,还病得不轻,都往出尿这些白虫子啦。放羊小子肯定地说,那放羊女子就吓得大哭了起来:妈呀,我怕是活不成啦!放羊小子又开口,说:罢罢,我这个人,最见不得女娃娃哭。你这么哇,要治你这种病,以前有个老羊倌倒是给我讲起过一个办法。放羊女子一听,拉住了放羊小子就不放手,说:那你快引我去见那老羊倌呀!放羊小子头摇得拨浪鼓一般,说:早死啦。放羊女子嚎啕大哭起来:妈妈呀。我没治了,活不成啦!放羊小子说:你也别嚎,嚎死了,你妈也救不了你,现在能救你的,这世上也只有一个人。放羊女子忙问:这个人……在哪儿?放羊小子: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放羊女子说:你一定不能见死不救。你快救我呀!这放羊小子却又为难起来,女子跪在放羊小子面前乞求:你就看在我俩都是放羊的,还处得不赖,救我一命吧!小女子会用一辈子来补报你!这个放羊小子没办法,只有舍身救人啦。几个月后,他说:好了。放羊女子“病”是好了,可肚子也大了,就只好嫁给了这个放羊小子。再后来,他们有了娃娃,那娃子一天挖了一窝蚂蚁蛋,他妈一看,傻了,这咋和她得病时尿出来的白虫子一模一样啊?!天星叔三岁死了娘,跟着他爹长大,村里人们说起这父子,就说:一双筷子两根光棍,真可怜啊!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好多好心人,都试图给天星叔踅摸一个媳妇,也有几个见过面,可到头来,用天星叔自个儿的话来说,就是:青石板上弹杏核,弹一个,蹦一个!天星叔大概也心里不好活。要不,嗓子本来不好从不唱曲的他,现在也常常在山坡野洼吼上两嗓子:人家骑马我骑猪,一肚子苦水给谁诉。一次,他还站在羊倌房子外,唱:有老婆的人儿早睡觉,没老婆的人儿满村村绕。为了讨天星叔的欢心,我真诚地凑过去对他说:天星叔,要是我是个女人,我就一定嫁给你做你的媳妇!天星叔抬腿就在我屁股上踹了一脚,将我踢出两丈远,还大骂了一句粗话:爬你妈的那个×。放暑假后,我就三天两头地去和天星叔混群放羊,到羊倌房子的次数也就更多了。这天夜里,睡到半夜,没听到呼噜声,我一骨碌坐起来,身边,天星叔睡着的铺,居然是空的。不过,被子还堆成有人仿佛在睡的样子,让我差点上当。天星叔哪去啦?我坐在炕上,怔怔了半晌,跳下地穿上鞋,就往羊倌房子外边跑,天上月明,可是门里门外,还有羊圈前后,哪有天星叔的影子?我张了几张嘴,没喊出声,再往远走,又不敢,最后只好回到羊倌房子,找到火柴将马灯点了,坐在灯下等。天星叔是天快亮时才回来的,带着夜露的气味。一进门吃惊地看我:你咋醒来啦?我嘴一扁,哭了出来:你去哪儿啦,半夜三更,荒山野岭,丢下人家一个人,吓死我啦!天星叔赶忙过来哄我:这么大人啦,怕甚?叔能去哪儿,睡着睡着,听到西崖那边有羊叫,怕是丢了羊,寻羊去了哇!我用手背抹着泪:真的?天星叔说:骗你有甚油水?就是群里最调皮的那个小黑山羯子嘛!而我明明记得天黑羊回圈时,那只小黑山羯子还顶了我的屁股一下……嘿,算了,天星叔已经钻进被子里呼呼大睡了。第二天半后晌,我们在西边的沙洼放羊时,突然看见对面的半坡上,蹲着一只狐狸,白白的,是我先看见的,没敢做声,赶快扯身边天星叔的衣袖,用下巴示意他。天星叔看到后,连忙丢了手中的羊鞭,跪下,向那狐狸双手作揖,嘴里还一连声地说着:成啦,成啦,大仙您熬成啦!那狐狸的头动了动,忽然转身,一条大尾巴在坡上一晃就不见了。我问天星叔,你刚才这是?天星叔这会儿连脸色都变了,欣喜地对我说:这你娃娃就不懂啦,这狐子,不,狐大仙可灵通着呢,他们在修炼,有的已经修了好几百年上千年啦,凡全白了的,恐怕就是修炼了上千年的,他们修成之时,还需接人的口气,谁要碰见了,一定要对它说:成啦成啦,大仙你修成啦!天星叔换了口气接着说:你这么一说,它就真的修成啦,成仙啦!这就叫接口气,口气接不对,它就还得再往下修,谨记,以后但凡看到有狐子向你打拱,你就赶快向它作揖,接口气:成啦成啦大仙你修成啦!我问,这与那狐狸是好,可对咱们,又有甚好处呢?天星叔:咦,看你这娃娃说的,有甚好处?那好处大啦!你想想,既然你接好口气,叫那狐子成仙了,它成了仙后呢,还能忘了你么?天星叔说着,又给我讲了两个狐大仙报恩的故事,忽又敛颜正色地问我:对了,我刚才没看清,那只狐子可是浑身全白?可是正向咱俩打拱?我就故意说:哪是甚么浑身全白,整个一个老杂毛。才不是向咱们打拱,是龇牙呢!天星叔一声喝住我,嘴里却向空中说:童言无忌,童言无忌。(秦永新原创摄影作品《娄烦马》)那天,我正在羊倌房子里,就着墙上的马灯看一本小人书,天星叔说是要去东崖下刘家借水桶,去井上担水,地脚的水瓮已沙拉沙拉刮瓮底了。我把一本小人书都从头看到尾了,天星叔还没回来。我正要出去看看,羊倌房子的门,被人一脚踢开,一个红脸汉子气咻咻地站在门口。我认出是刘秀,就忙依了乡里的辈分,笑着问:刘大爷,你来啦?刘秀茬儿也不搭,怒气冲冲地问我:我们家绊女子……没在你们这儿?我热脸贴了人家个冷屁股,心里也不高兴了,说:我们这儿是羊倌房子,哪有你家半个还是整个女子?红脸汉子狠狠地瞪我一眼,说:球大大个人,别想骗老子!我也火了,就吼:骗你?我平白无故骗你做甚!就这么点地方,不信,你尽管自个儿看了哇!不到一间大的个屋子,一眼看到底。红脸刘秀又问:杨天星那个货呢?我扭转头,半天才说:杨天星又不是你家的甚么人,你管着他呢。说到这儿,我又忽想起他毕竟是个大人,才又补充说:他不是去你家借桶担水去了么?红脸刘秀双脚在门口重重地跺了几下,转身就走。不一会儿,天星叔回来,并没见他担水,赤着手,一条裤腿上还湿了一大片。我就讲了刚才刘秀来这儿找绊女子的事,还把我如何大胆顶撞刘秀的话儿,向他学说了一遍。没想到天星叔却甚么话也没说,没问。管自蹲在地脚,卷了旱烟,大口大口地抽。直到将整个羊倌房子抽得像着了火,我不得不下地打开门放烟。天星叔起身出去尿了一道,回来就上炕睡下,连衣裳也没脱。那一夜,再没有听到他说一句话,我也就没敢再多嘴多舌,那是我在羊倌房子过的最沉闷最没意思的一夜。天星叔终于出下事了。那是那年的深秋,天上有一列列人字形的大雁南飞。我放学回来,又去西沟给父亲送饭。一到那里,我就感觉到气氛不对,天星叔耷拉着个头,在树下唉声叹气,父亲则扭着个脖子,不知往哪里看。知道我要回家时,父亲突然说:让这小子也在,做个见证!我叫闹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就留了下来,与他们一起混群放羊。这天后晌,我才闹清究竟出了甚么事儿,原来,昨天晚上,本该父亲与天星叔在羊倌房子过夜,可家里小妹突然上吐下泻,母亲叫我站在崖畔,隔沟喊着,将父亲从羊倌房子叫回,这样,那里就留下天星叔一个人过夜。鸡叫时,那红脸刘秀又踢开门,天星叔的被子里却有两个人……这一下,那红脸汉子就不依不饶啦,今天晚上已叫了我们的队长赵四来,看这事儿到底该怎么办?私了还是公办?这天,太阳还没落山,父亲就打回头羊,往羊倌房子那儿去了。天星叔一个人,远远地落在羊群后头,好像鬼拉了他的后腿。父亲低声吩咐我说:到时候,说起来,你就一口咬定,是那绊女子自己老往羊倌房子跑的,记住了没?我也拧了拧脖子对父亲说:这还用着你安顿?接下来,夜里在羊倌房子的场面,可以说是“三堂会审”,我们这边,除天星叔,有父亲、队长赵四、再加上我,女方那边,则是红脸汉刘秀,她老婆马兰,外加他们生产队的队长魏二。绊女子眼睛哭得都肿成了两个桃子,还是被他爹逼着来了,却不进屋,在门外和羊圈连着的黄泥墙脚下坐下了,双肘支在自己的双膝上,托着头,抽抽咽咽。我们队长赵四提起水瓮后边的煤油瓶,往马灯里添了一回油,将灯头拧得大大的,又从地下提起一个破化肥袋子,手探进去,一摸,一瓶酒,再掏,是一瓶水果罐头……一共一瓶酒,三瓶罐头。最后,还从身上掏出两盒“凯歌”牌纸烟。赵四将东西摆到小炕头上,先撕开一盒烟,第一个给魏队长递,接下来,红脸刘秀,最后我父亲,就没给天星叔。赵四又划着火柴给每个人点了烟,轮到自己,火柴燃尽了,他就又划了一根。烟只抽了两口,赶忙在鞋底上擦熄,别在耳朵上,忙手忙脚地往开打罐头,开酒瓶,嘴上说:就算出下天大的事儿,咱也都是些里湾湾的人,本乡田地,抬头不见低头见,有甚事儿不能好好儿坐下来说的呢?魏队长……二哥,你说呢?那魏队长一看就是个馋酒的,他先接住倒了半缸酒的搪瓷缸子,美美地喝了一口,还“哈呀”地舒服地叫了声,才点着头说:就是,就是嘛!赵四又逼着刘秀也喝下一口酒,自个儿才往炕沿上一坐,背靠墙,仰起头说:刘大兄弟,那今天我看你就先开金口吧!魏队长晃晃酒缸子说:我们……都是应你叫来的,就你说!刘秀抽完第一支烟自己又抽了一支,点了,默默地吸了半截,终于开口,说:你们队也是,好好儿的,盖这个破羊倌房子做甚!我们一家在这儿,一直清清静静的,你们盖了这破房子,倒好,又要捡我们的柴,又要担我们的水,连做饭缺油少盐还要向我家借……一来二去,这不,就弄下这好事儿了吧!赵四手在面前一伸,说:咱今天打烂盆说盆,打烂罐说罐,千万不要扯那些没用的,对不对?魏队长响应:这话没错!刘秀不高兴了,说:这凡事都有个根由不是,要不是因为你们盖了这个破羊倌房子,这丑事儿咋能出下。好,那咱今天就赶捷径说,今天一大早,鸡叫时分,我起来尿,觉得不对,再看,我们家绊女子的盖体里是空的,可把我吓了一大跳,这灰女子,深更半夜,能跑到哪去,我连老婆也没招呼一声。刘秀说着推推老婆,老婆赶紧点头:唔,就是,可不是!刘秀继续说:一出家门,我心里就揭底精明了,拔腿往这儿来,一脚踢开门,果不其然,他们……刘秀抬手直指地脚的天星叔,说:杨天星,你以为你大你妈给你安上个人头,你就是人?你是牲口、毛驴,你毛驴都不是个好毛驴,我们家绊女子今年才多大,十八,你呢,快三十岁的老毛驴啦,把人家黄花闺女当自个儿的老婆睡,你咋能下了这手来啊?啊?!不管刘秀咋么骂,天星叔只有一句话:反正都是你家女子她自己来的,我从没去你家勾引过她!我看到父亲在腰后捅我,就赶忙站出来为天星叔作证:就是,我和天星叔不知在这儿过了多少次夜,每次都是绊女子自个儿来,一来就缠着我天星叔给她叨古今,不信,你问你家女子,我要说假话,不姓张跟你姓呀。刘秀先骂,跟着刘秀老婆骂,魏队长、赵队长也做腔跟着骂,骂到底,天星叔就那一句话:是绊女子她自己来的。看看一瓶酒已见底了,三瓶罐头,也你一块我一口,吃得差不多了,夜已深了,赵四起身坐正了,说:说到明天这会儿,这事也就这么点事儿,咱说也说够了,骂也骂够了,现在依我看,就一句话:这事儿到究咋办呀?魏队长已喝得有些多,说:快说,明天还事儿多呢!话又赶到了刘秀那儿,刘秀头一勾,说:这事儿咋办?我看没那么好办,我们家绊女子,好好儿一个十八岁的黄花大闺女,叫天星这狗东西给闺女闹成媳妇啦,更何况我们家女子可是订了婚的,这事儿要是让人家婆家知道……赵四一拍大腿,手指刘秀说:嘿,都说了你们一面面儿的理啦,你说我们天星把你家绊女子黄花闺女闹成媳妇啦,那我还要说,是你家闺女把我们这囫囵后生子弹打成弹壳啦!是不是?父亲听了,扑哧笑了,赶忙又收口说:可不是嘛,别看我们这后生年龄大了点儿,可他以前就是一个原封大后生,童男子,这……我敢用自己的吃饭圪蛋来担保!他指划自己的脑袋。这一下,就真把刘秀两口子都说住了。赵四趁热打铁,说:说成甚,我们天星也没有去你家勾引你家女子,你刚才不是也说,你是今天早晨在这羊倌房子里捉住他们的嘛!这不是你家女子自己送上门来是甚?趁对方无话时,赵四又说了一句:这要是在你们家闺女被窝捉住了我们的人,那我赵四今天保证屁也不放一个,由你们一根绳子把杨天星他送到公社送进公安局去!刘秀老婆又哭了起来,说:那,我们家绊女子今后咋呀,那么闹,还怕闹不上肚子,绊女子如今怕是已经有了……这可咋向人家婆家交代呀,真是丢死老刘家的先人啦!那天夜里这事儿,真还一直闹到鸡叫头遍。最后还是队长赵四做了了结:要么,尽管把这事儿张扬出去,保证对谁也没好处,天星坏了名声,顶上打一辈子光棍,你家女子,有了这名声,就算嫁出去了,恐怕今后也不会有好日子;要么,干脆来他个就坡下驴,赶快将那边的婚约退了,所有彩礼都由天星家来拆补,再选上一个好日子,把绊女子嫁给天星。就这。赵四丢下这番话,拉门第一个走了。让我、父亲,包括天星叔本人也没想到的是,这件事儿的结果,最后,真还按赵四说的那样:三天后,刘家主动把女儿那桩婚约退了,冬天就把绊女子嫁给了杨天星。成亲那天,绊女子穿了一身大红棉袄,从彩车上下来,赵四亲自伸着两条胳膊,对守在大门二门口准备耍新娘子的人们说:今天都得听我的,稍微耍一下,意思到了就行了,新媳妇身重,不方便!说着,赵四亲自护着身子笨重的绊女子进了洞房。夜里闹洞房时,我冲在最前,吵着闹着要新郎和新媳妇给糖,天星开始只给一块两块,后来,我冲他喊了一声:羊倌房子——,他一下子脸变得通红,抓了一大把水果糖来堵我的嘴。张秉毅,祖籍山西河曲县,供职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文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小说和电影剧本创作。小说代表作有《黄土高坡》《旧乡》,电影剧本代表作《牛女》《漫瀚调》《回乡种田》等。来源:山西文学更多新闻
公告
年度鄂尔多斯市城乡居民基本医保个人缴费标准变了!
本期编辑:刘浩东
校对:刘浩
点“在看”让更多人看到!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