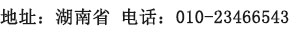那天夜里,急诊,住院,次日一堆检查。大夫们围着我,问我生病前做什么。
我努力回忆,想不起生病前做过什么特殊的事情。事实上,生病前做的事情都是这些年来每天做的。白天一半的时间给家里,一半时间给学校,晚上看书查资料写文章,凌晨三点左右睡觉,早晨八九点钟起床。大夫们皱着眉头听完,只能把病因归咎于熬夜。
又问我最近半年是否去过外地,我点头,半年内去过四川省阿坝州的草原,住在牧民家里做调查做访谈。我话毕,大夫们后退半步,眉头皱得更紧了:“怕是布鲁氏杆菌”。看他们的表情我就知道大事不妙。布鲁氏杆菌,一种牲畜间互相传染的病菌,有时也从牲畜传染给人,人与人之间不传染。甘肃、青海、四川的牧区是布鲁氏杆菌的高发区,常见于和牛有过密切接触的人。我点点头,是的,我很喜欢牛,近距离拍过照、画过素描、抚摸过牛。
我突然感到非常非常沮丧。一方面,倘若确诊布鲁氏杆菌,治疗周期会很长,医院里。另一方面,我喜欢草原,喜欢我做田野调查的那个地方,倘若不能再去草原,我的毕业论文怎么办?击垮一个博士研究生的致命弱点是他的论文,我就像拳皇里被KO的游戏人物一样瘫在病床上,万念俱灰,身体都快变成半透明的。
抽了血送去其他检测机构,谢天谢地,阴性,排除布鲁氏杆菌的可能性。
又做了腰穿,抽取脑脊液,排除了颅内感染的可能性。
做了CT,大夫说:“巨浪,你的肺就像一件破棉袄。”
手上扎留置针,就是一根针,一直留在血管里,手臂外面露着一条塑料管。每次输液,针扎进塑料管,就不必每次都要在手臂上找血管。留置针用得时间久了,血管就会变得脆弱,药液会漏进血管附近的肌肉,让手臂疼痛和肿胀。留置针在左臂几天,再换到右臂,右臂血管不能用了,再换左臂。住院十多天后,两条手臂都肿胀得无法抬高或放低,连穿衣服都要家人辅助。后来我央求护士,试试在我腿上扎。
护士有两类,漂亮护士和不漂亮护士。每次见到漂亮护士,我都会很害怕,因为但凡漂亮护士的手艺都很差,扎针总是不准。有个穿粉红色制服的实习护士最让我胆寒,有一次她执着地要在我手臂上找血管,我恳求她试试腿,因为我手臂肿胀得厉害,腿上的血管好扎一点。她完全无视我的请求。我理解,小姑娘嘛,都有洁癖,扎病人的手总比扎病人的脚看上去“干净”一点。她最终选择了我左手大拇指的一根血管,扎了两针,鲜血直冒。她拔了半截,企图再扎,我疼得招架不住,央求她放了我。她气愤地拔了针,出门找别的护士。
医院里,医生和护士是两个物种。我经常见到一群护士一起走路,或者见到一群医生一起走路。可是任何时候,都不会见到一群医生和一群护士混杂在一起,更不可能见到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并排行走。医生和护士好像使用两种不一样的语言,他们之间唯一的交集是医嘱单。医生写点什么冷冰冰地交给护士,护士写点什么冷冰冰地交给医生。
堂弟是个规培医生(医学院毕业的学生要经过三年规范化培训才能成为正式的医生),找对象是全家长辈发愁的问题。大学五年,规培一年,长辈们期待的那个女孩始终没有出现,堂弟每次去电影院都是一个人。“医院里那么多护士,你咋不追一个呢?”奶奶忍不住问他。“你不懂,医生和护士是两个世界里的人。”他说。我以前也不懂,医院,有点懂了。
以前生病都是硬扛,这次没扛过去,或许是个好事。这次疾病给了我一个警告,让我意识到自己不再是少年时想象中的那个硬汉。青春期时代,想象中的自己应该是“印第安纳·琼斯”那样的:左边腰带挂一支左轮,右边腰带挂一卷绳索,一边行侠仗义,一边从事考古发掘。现实中也真的像印第安纳·琼斯那样驱使自己的躯壳,走南闯北,半夜不睡,左兜素描本,右兜录音笔,看到美景就画,逮到老头就采访口述史。生病前的这段时间,白天搬家,再重的书箱也要自己扛上楼。夜里写字,刚扛上楼的书箱就拆开,挑出资料翻开查阅。
终于,一个月前的一天,我轰地瘫倒在病床里,过了好多天才搞清楚状况。
疾病就像摇骰子,摇到你就是你,不许废话。
你不服气,大声抗辩:凭什么是我?我又不抽烟,也不喝酒,也没干坏事,虽然偶尔熬夜,可是好多人熬得比我厉害也没事呀!
命运之神没心思听你啰嗦,一巴掌把你拍晕,你就自个儿躺着去吧。
住院很多天后,一天晚上吃饭,吃着吃着哭了起来。高烧一个星期,那天下午终于降到38度以下,头不疼了,吃饭能感觉到饭香。饭真香啊!我从没吃过那么香的米饭,就是普普通通的米饭,普普通通的炒油菜。
在那天晚上之前的两个星期里,吃饭就是一项政治任务,要凭毅力。生病的头三四天,我什么都吃不下。有一天输液时,大夫发现我的血管萎缩得厉害,前一天还能用的一条血管,第二天已经扎不进针了。大夫说:你要好好吃饭,不然连输液都困难。后来我就逼自己:再吃一口,再吃一口。
那天感觉到饭香,顾不得家人都在身边,嚎啕大哭了一阵。疾病会让人变得敏感,会被极小的一件事感动得流泪。
有一天,媳妇陪我,怕我孤单,给我唱歌听。她唱完,让我也唱一首。我就唱了宋冬野的《安和桥》,前面还好,唱到“我知道,那些夏天,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代替梦想的也只能是勉为其难”那一句时,我又掉眼泪。媳妇说咋了呀,又哭,谁惹你了。我说这个词写得太他妈的好了。你看,我生病前计划了好多事情没做完,我和师兄师妹约了要去青海化隆做调查,出发前三天病倒了。生病第一天还以为,睡一觉能好,然后归队去做调查。医院住了这么久。生病前多么牛逼的研究计划,躺在病床上都是扯蛋。雪季马上要到了,我的滑雪伙伴们都在约“下周滑雪哟”,得了,肺炎一过,我这个冬天都不能再上山了。还有啊,我去过的那些好玩的地方,国家,城市,我都答应要带你再走一遍,现在不都“吹过的牛逼变成一笑了之”了吗?
关于疾病和健康的大道理,谁都听过,朋友圈里的养生贴,谁都见过。可只有被疾病砸晕一回,你才会把那些大道理当回事。清晨起床,黄河边那些跑步健身的人,十有八九都是曾经大病过一场的。那些健康的身躯,还在酒吧里买醉,还在办公室里赶材料,还在阴冷的自习室里抄笔记。
医院清洁工每次打扫我的病床周围时,我都说声谢谢,时间久了,她就和我说说话,有时聊聊她在远方上学的儿子。她也肺不好,每清扫完一间病房就咳一阵。她说08年大病了一场,整天整夜发烧,烧得不省人事。“人经历了生死就知道什么东西最珍贵了。”
有一天说得比往常多,临走前说:“小伙子,你的病不算重,将来出院多锻炼,不要被这点小坎坷打倒。”
次日早晨清洁工再来时,医院换清洁工了。新来的清洁工很热情地和我打招呼:你好!吃过饭了吗?需要我给你一个新垃圾袋吗?不用谢!我应该做的。
我猜,大概她的前辈临走前和她说过,一号床的病人脾气好。
每一次量体温都像彩票开奖。
医学上,当人体体温高于37.3度时,就判定为发烧。当体温高于38度时,判定为高烧。换了好几种药,药的威力越来越强,大夫、护士、家人都焦急地等待我降温。体温忽高忽低,波动着下降,每天比前一天略低0.1、0.2度。终于有一天,彩票开奖,开出一个36.9,终于破37大关了!我把数字念给护士听时,连门外路过的护士都为我喝彩:“真是个好消息。”
大夫来查房时,我的主治大夫也高兴地祝贺:“听说你今天突破37了。”大夫希望我的体温保持在36.x范围内,才算标准地回归“正常”。
我的主治大夫姓马,回族,得知我的专业是民族学时,非常感兴趣,有时会找我聊两句民族学。我就努力地回忆我在穆斯林地区做过的调研,讲讲尔麦里、太斯米、者玛提,讲讲门宦、塔布力赫、三抬,讲讲哈俩里、哈拉姆、筵席章。有时和伊斯兰教有关的调研经历讲完了,就后悔和马文奎、马志强哥俩吹牛扯蛋时,他们讲过那么多好玩的故事都没记住。实在没谈资,我就讲讲多卫康、前弘期、中观论,或者讲讲阿育王、出埃及、法利赛人。马大夫依然听得津津有味。末了,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好深奥呀”。大概是术业有专攻,或许在其他专业的人眼中,我们所学的这些东西是颇有趣味的。
医院里的趣事。看我每天努力量体温,恨不得随时夹着体温计,他告诉我,有不少病人和我相反,努力地装病。“怎么还有这种病人?”——可不是,那些年轻战士来住院,能住多久住多久,不然病愈出院就要归队训练。反正看病国家报销,一些人就设法伪造体温,比如把体温计在热水里蘸一蘸,蘸够38度再加进腋窝。还有的喊头疼,做检查一切正常,可病人就是莫名其妙头疼。对于这些病人,大夫们明知有鬼,可也只能无可奈何地让他们继续住院。他十分愤慨——“那些边防战士有病无法就医,城里的战士躺在病房里浪费医疗资源”,医院里存在的这些问题,他什么都改变不了。
——你能研究这个不?
——呃,我不敢,也不是我的专业。
肺炎三十天,前半个月,我都浑浑噩噩在病床上躺着。我很担心有人来看我,因为客人来了就要说话,说话就要咳嗽。有时亲友们来看望我,我就伸出手和他们握一下,继续躺着发呆。
后半个月,我稍微有点精神,就想看书。我对媳妇说,记不记得我刚生病的时候你帮我取过几次快递?她说都在家里扔着呢,包装也没开。我说都是书,你随便开一包,带一本来。她带了两册NationalGeographic的杂志。后来看完,又让她从书架上随便抽一本。她抽了一本《清史稿》。
医生不许我看书,因为看书会耽误休息,见到我看书就催促:快收起来。有一天医生护士都没有制止我看书,我就抱着清史稿读了整个一下午,二十多天都没读过书了,真过瘾。那天还想到了不少有趣的问题,把读书心得写在朋友圈里。结果当天晚上果然失眠,大脑太兴奋了,总在想问题。辗转反侧,寤寐思服。
后来读书都悠着,有时想看书时忍着,先摸一摸书皮解馋,就好像老烟鬼想抽烟时闻一闻烟盒。
刚住院时,知道住院部楼下有个人工湖,一直心心念念:等将来恢复健康,一定要绕着湖跑两圈。家人知道我的愿望,就替我侦查了一趟,带回来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人工湖是一潭死水,闻起来味道不怎么样,表面浮着一层油脂。
唉!
终于捱到出院那一天,我被裹成一个严严实实的大粽子,如同电影里的大护法。小心翼翼地踏出住院大楼,呼吸到二十多天来第一口户外的新鲜空气,哇,好凉,好舒服。认清方向后,我就迫不及待地告诉父母:走!陪我看一眼人工湖。
走近看了几分钟,慢慢地沿着湖边走了几步,还不是太糟。一个月的时间,湖面结了冰,冰上又落了厚厚的枯叶。原来我病了这么久,湖水都结了冰。一年的十分之一,就这样过去了。
赞赏